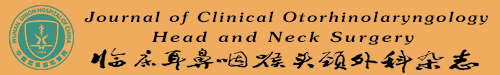主持人:余力生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点评讨论嘉宾:杨仕明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余力生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王秋菊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李明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发言嘉宾:高下教授(南京鼓楼医院),张剑宁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刘宏建教授(河南省人民医院),曾祥丽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张劲教授(博鳌恒大国际医院),姜子刚教授(秦皇岛市第一医院),王慧教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杨蓓蓓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冰丹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王方园教授(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左汶奇教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俞艳萍教授(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刘晖教授(陕西省人民医院),宋勇莉教授(西京医院),宋纪军教授(周口市中心医院),王明明教授(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组稿:马鑫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陈钢钢教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张甦琳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余力生教授:
耳鸣一词源于拉丁语“tinnire”,意思是“ring”,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至少经历过一次耳鸣,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耳鸣会在几秒、几分钟或几小时后消失,但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耳鸣持续,并影响生活。声音不仅对语言的发育和交流起重要作用,还有重要的警示作用,经验会赋予声音不同的含义,因此不同的声音会引起不同的情绪反应。耳鸣虽为无意义的声音,但同样会引起各种不同的体验,包括各种情绪反应、压力、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部分耳鸣可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近几年国内对耳鸣逐渐关注,不可否认,耳鸣确实有很多未解之谜。此次圆桌论坛,将从耳鸣概念、分类、机制、相关因素、治疗等方面展示各位专家有关耳鸣的学术观点,首先梳理已经达成共识的、值得推广的耳鸣观点,其次梳理有待解决的耳鸣难题,指明未来临床及基础研究的方向,逐步破解耳鸣谜题。
1. 耳鸣的几个概念
马鑫教授:耳鸣的发病率逐渐增加,McCormack等[1]对1980—2015年文献进行了综述,耳鸣的发病率为5.1%~42.7%,中国大陆耳鸣的发病率与全球数据一致,为4.3%~51.33%,数据分散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同研究使用的标准不同。临床中医生和患者使用的耳鸣概念非常宽泛,明确耳鸣相关的几个概念,对推广交流观念、经验都非常重要。①幻听:指没有客观声源情况下有意义的声音感受,该主诉目前属于精神科范畴,不在讨论之列,但临床中应首先识别。②耳内噪声:指伴有暂时听力下降的突发耳内噪声,常单侧随机出现,无预兆,发作时可伴耳闷感,多持续1 min左右消失,这种一过性耳内噪声也称为短暂的自发性耳鸣,2014年美国耳鸣指南将其列为正常生理现象。③客观性耳鸣:有真正的物理性声波振动存在,可被他人觉察或用仪器记录的耳鸣,包括血管源性、肌肉源性和呼吸源性。客观性耳鸣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目前临床疗效比较好的耳鸣类型,需要优先识别。④主观性耳鸣:没有客观声源、无意义的声音感受,占耳鸣患者的绝大多数,目前诊治困惑较多。a.生理性主观性耳鸣:正常人堵塞双耳或在非常安静或隔声室内可感受到耳鸣;b.病理性主观性耳鸣:McCormack等[1]共搜索5个数据库,纳入报告39个不同研究,其中耳鸣有8种不同类型的定义,最常见的是“耳鸣持续时间超过5 min”(34.3%)。只有七项研究为所使用的问题给出了理由,或承认缺乏关于耳鸣的标准问题。在耳鸣的定义和报告方面普遍不一致,导致各研究对耳鸣流行率的估计存在差异。病理性耳鸣的定义一直未统一,一般认为持续5 min以上,且1周内反复出现的耳鸣才属病理性。⑤主观性耳鸣的病因分类: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a.原发性主观性耳鸣:指伴或不伴感音神经性聋、不能找到明确原因的耳鸣。b:继发性主观性耳鸣:除感音神经性聋之外,有较为明确潜在病因的耳鸣,比如外耳道耵聍栓塞、外耳道异物、外耳道胆脂瘤、外耳道湿疹等,中耳分泌性中耳炎、慢性中耳乳突炎、中耳胆脂瘤、粘连性中耳炎、中耳胆固醇肉芽肿、耳硬化症等,内耳常见疾病梅尼埃病、听神经瘤等,且在病因治疗后,耳鸣常减轻或消失。⑥主观性耳鸣病程分类:分为急性耳鸣、慢性代偿性耳鸣(非恼人耳鸣)和慢性失代偿性耳鸣(恼人耳鸣)。a.急性耳鸣:我国多以6个月以内为急性耳鸣,6~12个月为亚急性耳鸣,12个月以上为慢性耳鸣;美国2014年指南以6个月作为急慢性耳鸣分类标准;欧洲耳鸣指南以3个月以内为急性耳鸣,3~6个月为亚急性耳鸣,超过6个月为慢性耳鸣。b.慢性代偿性耳鸣:耳鸣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无明显影响,但可以引起患者对病因的好奇,以及对病情演变和耳鸣是否会进展和改变的担心。c.慢性失代偿性耳鸣:患者痛苦,影响其生活质量和/或健康功能状态,患者积极寻求治疗和干预策略以减轻耳鸣。
点评:
余力生教授:关于急慢性耳鸣的划分,不仅涉及预后,还涉及耳鸣的机制。很多文献证实,耳鸣和疼痛非常相似,疼痛的研究远比耳鸣广泛深入,可供借鉴。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在病因学、发生机制、病理生理学、症状学、诊断、治疗上有明显差异,急性疼痛是疾病的一种症状,是机体受到伤害的警告;而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且慢性疼痛中有很多是“虚假警报”,并非真正的“伤害警报”。耳鸣亦如此,急性耳鸣是一种症状,是身体的警铃,应积极寻找引起耳鸣的原因;而慢性耳鸣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因此对耳鸣进行病程分类对于制定治疗策略、预期治疗效果意义重大。
关于急慢性耳鸣的时间节点,有很大的探讨空间。我们曾对突聋后的残余耳鸣进行随访,相当比例在1~2年后开始感觉逐渐适应耳鸣,这也提示我们,单因素(比如突发性聋)引起的耳鸣,在听力没有恢复的情况下,耳鸣代偿需要较长的时间,并不是超过6个月的耳鸣就好不了。所以面对急性耳鸣患者,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给中枢对耳鸣代偿的时间,不要武断地过早对患者下“神经性耳鸣”的结论,更不要武断地告诉患者慢性耳鸣好不了,这种负面的咨询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恐慌和焦虑而更加关注耳鸣,从而大大影响了耳鸣的代偿过程。也有研究显示,中枢的重塑,早期主要以功能性改变为主,大概4年以后,涉及区域可能发生结构性改变,这点在微血管减压和经颅磁刺激中得到证实,而一旦发生结构性改变,则提示预后不佳。如果急慢性耳鸣的分界是为了提示预后,可能时间长一些更合适,给患者和医生足够的时间,如果说4年较长,推荐1年更合适,当然这还需要大量的基础工作进行证实。
王秋菊教授:急性耳鸣的时间划分倾向于欧洲耳鸣指南,即3个月内为急性耳鸣,3~6个月为亚急性耳鸣,超过6个月为慢性耳鸣。所谓的急性耳鸣一定是在近期出现的新症状,耳鸣的出现提示的是一个紧急事件的信号,提醒患者需要及时就医,并围绕耳鸣症状进行耳鼻咽喉头颈相关区域的检查和疾病的鉴别,同时进行生活方式、精神状态、饮食情况、睡眠状况的系统分析,以便于早期发现导致急性耳鸣的可能病因,从而开展积极的治疗,以期解决或缓解耳鸣病症。对于6个月以上的慢性耳鸣,详实的专科检查和生活方式的调整也尤为重要,加强对耳鸣的综合管理而不是完全不予以干预或认为无法治疗,需要理念上的更新和改变。
李明教授:耳鸣分期在临床的确非常重要,这是因为指导治疗的需要。2012年耳鸣专家共识的观点是3个月以内为急性,也是患者最不舒服、很容易加重的阶段,当然也是治疗的最佳时期;4~12个月是亚急性期,此期只要患者没有经过正规治疗,就可采用急性期方案补救性治疗;超过1年即为慢性耳鸣。这个分期临床使用多年,大家正在接受中,是否需要修改也请各位专家拿出实实在在的数据,而不是参照国外资料。我们已经过20余年的实践,各大医院、各级医师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耳鸣临床或基础研究中来,发表的耳鸣相关文章数以万计,应该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立认知和思想,不能人云亦云。尤其在中国我们是以医生为治疗主体的体系,具有处方权,可以对耳鸣患者进行及时、随时的检查和处置以缩短适应耳鸣的时间。这在国外是做不到的,也是重大差别之处,却对耳鸣患者非常重要。
总结:①临床中面对耳鸣主诉的患者,首先要区分是幻听、主观性耳鸣还是客观性耳鸣,进入不同的诊疗路径。②特发性主观性耳鸣是临床发病率最高、最困惑的一类耳鸣,首先除外继发性,原发性耳鸣则推荐按照分期治疗。③特发性主观性耳鸣如何按照病程分期很重要,对指导治疗和预估预后很有意义。目前各国指南和专家观点仍有不同,3个月、6个月,还是1年,尚需要证据,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急性期以消除耳鸣为目的,随着病程延长,重点则为治疗耳鸣伴发症状。
2. 客观性耳鸣目前机制清楚,可以给予针对性处理,需要优先识别
姜子刚教授:客观性耳鸣值得关注,可分为肌源性、血管源性、肿瘤性及其他类型。①肌源性多由中耳肌、腭部肌等痉挛所致。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需排除继发的源头疾病,如腭肌阵挛常与Guillain-Mollaret三角病变相关,中耳肌阵挛可与多发性硬化致脑干脱髓鞘相关。鼻咽部及软腭部检查有必要,导抗图及声反射可见锯齿波、腭肌来源更明显。长时程声导纳监测可动态观察10~15 s内中耳声导纳的变化,提高诊断准确性。原发性的治疗包括口服药物、心理治疗、放松疗法、催眠疗法、噪声掩蔽、针灸、局部封闭、局部注射肉毒素A等,多不主张手术。②血管源性分为静脉性与动脉性,搏动频率与脉搏一致。静脉性者多见颅内静脉窦狭窄、特发性高颅压、乙状窦或颈静脉球区骨壁缺如或憩室、乳突导血静脉异常等;动脉性者可为颅内外动脉畸形、动脉粥样硬化、迷走颈内动脉、颈动脉纤维肌性发育异常、颈动脉内膜剥脱及夹层、颈外动脉狭窄、永存镫骨动脉等。动静脉瘘以硬脑膜动静脉瘘、颈内动脉海绵窦瘘为多见。颞骨双期增强CT、MRA、MRV、DSA等有助于诊断。患者影像学检查发现血管异常,并不能排除其他病因存在的可能性。③肿瘤性者行影像学检查易被发现。④其他类型中咽鼓管异常开放、Paget骨病、高动力循环状态(贫血、甲亢、妊娠、高血压)等需要注意。Paget骨病是慢性进行性局灶性骨代谢异常疾病,以骨痛、骨畸形、骨折及局部皮肤发热等为特点,可出现搏动性耳鸣。注意不要与Paget病混淆,其又名湿疹样癌,多发生于乳头部位,临床以顽固性湿疹样皮损表现为特点。
王明明教授:急性低频感音神经性聋(acute low-tone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以刮风样耳鸣、耳闷胀感、听声回音为临床三大症状,是突发性聋的一种特殊类型,也可能是梅尼埃病、听神经病、自身免疫性内耳病等疾病的早期。因其独特的发病机制和临床特征,近年逐渐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疾病。注意需与血管搏动性耳鸣相鉴别,在患者叙述不清、常规纯音测听显示轻度低频听力损失时,可按压颈部血管进行纯音测试以鉴别。
点评:
余力生教授:镫骨肌阵挛引起的肌源性耳鸣,多继发于面瘫以后,卡马西平常有效。关于血管搏动性耳鸣:所有可导致头面部(包括中耳)血管扩张的疾病均可诱发静脉源性血管搏动性耳鸣。最常见的病因包括中枢敏化综合征(包括偏头痛)[2]、各种类型的中耳炎(隐匿性中耳炎、中耳胆固醇肉芽肿等)、胃酸反流、咽鼓管功能障碍等。值得注意的是:各种乳突术中常见乙状窦表面骨质缺损,但是没有搏动性耳鸣。说明单纯乙状窦表面骨质缺损不会导致搏动性耳鸣,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至于乙状窦手术后耳鸣可短暂减轻或消失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手术破坏了中耳血管所致,而非修补乙状窦表面的骨质缺损。如果病因未除,复发率会很高。呼吸源性耳鸣常见原因咽鼓管异常开放可能是目前临床低估的疾病,需要引起重视。
王秋菊教授:客观性耳鸣中较为常见的是血管搏动性耳鸣,其特点是耳鸣的节奏与心跳/脉搏的节律一致,可分为动脉源性搏动性耳鸣和静脉源性搏动性耳鸣。临床上可用颈静脉压迫试验来区别:如果搏动性耳鸣为静脉性的,做同侧颈内静脉指压试验,耳鸣将会减轻或完全消失;与颈内动脉或颈外动脉有关的搏动性耳鸣,在压迫颈总动脉时耳鸣会发生改变或减弱。静脉源性搏动性耳鸣需要与乙状窦病变(如乙状窦憩室、乙状窦骨壁缺损)、颈静脉球高位、特发性颅内高压综合征、颈静脉球体瘤、鼓室球体瘤等相鉴别。在诊断方面,可参考2013年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头颈学组推荐的《搏动性耳鸣影像学检查方法与路径指南》[3]:①首选颞骨增强CT(动脉期和静脉期成像);②行全脑增强MRA/ MRV,采集动脉、静脉系统的血管图像;③颞骨HRCT可清晰显示复杂的解剖结构及细微的骨质改变,如乙状窦沟骨板缺损;④内耳MRI,适用于CT、双期增强CT和DSA均没有发现异常患者或肿瘤患者;⑤全脑DSA,用于怀疑动静脉畸形、动静脉瘘或富血供性肿瘤患者。上述不同检查方法各有特点,需要在临床中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影像学检查方法。治疗主要包括手术治疗、介入治疗、药物治疗和其他治疗。
李明教授:静脉性血管搏动性耳鸣的病理从解剖来说已经比较明确,多发生在横窦向乙状窦移行部位,此部位与血流形式和速度有关。是以乙状窦憩室形成为代表的一类耳鸣,也由于介入手段的提高其逐渐扩展到乳突共鸣腔和横窦狭窄导致血流演变成湍流,可导致单侧或双侧搏动性耳鸣。这显然与涉及到是否会暴露乙状窦的中耳手术、后鼓室径路、内淋巴囊减压手术,以及乙状窦前径路桥小脑角手术等有很大不同,虽然暴露了乙状窦但手术后均未出现搏动性耳鸣,其局部解剖是宽敞的,而乙状窦憩室却是横窦移行形成乙状窦的特殊部位,极不规则、扭曲、狭窄致其形成湍流。
总结:①客观性搏动性耳鸣最常见的为血管源性,可参考2013年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头颈学组推荐的《搏动性耳鸣影像学检查方法与路径指南》,寻找责任血管。②除了影像可以发现的明显血管异常,注意要与良性颅高压进行鉴别,也要注意中耳乳突血管扩张对搏动性耳鸣的影响,尤其是仅有乙状窦骨质缺损而无乙状窦憩室的患者。③反流等因素对咽鼓管的影响非常值得重视。④呼吸源性耳鸣常见原因咽鼓管异常开放可能是目前临床低估的疾病,需要引起重视。
3. 主观性耳鸣的发病机制
王方园教授:耳鸣的发生发展机制非常复杂。其产生可能与外周听觉系统的损伤有关,但慢性化和维持的过程不仅有听觉系统参与,更是多种脑区共同作用的结果。耳蜗核是所有耳蜗传入神经纤维的终止处,也是听觉投射系统中第一级神经突触的发生地,其主要作用是收集内耳毛细胞传导的听觉信息,同时整合传入的体感及前庭信息,将传入的不论是抑制性信号还是兴奋性信号整合传入到下一级神经元,在听觉传导及定位中起到重要作用。由于噪声、药物等因素导致耳蜗受损后,在多种复杂机制的作用下,机体出现了耳鸣特征性的表现,主要为耳蜗核主神经元细胞自发电活动的增强、同步性增加以及刺激时间依赖性的神经可塑性改变等变化,最终这种变化经下丘传递至听皮层,然后被处理为一种无意义的杂声,这就是耳鸣。这个过程由多种配体门控型离子通道和电压门控型离子通道共同参与,这就是耳蜗核通过听觉系统参与耳鸣的产生过程。除了接受听觉信息外,耳蜗核还接收来自三叉神经感觉支的信息传入,也与耳鸣发生发展具有密切关系。耳蜗核接收的体感刺激主要来自三叉神经眼支以及三叉神经脊束核这两个区域(Sp5I和Sp5C)。体感神经元主要通过囊泡谷氨酸转运体与耳蜗核进行信息交换,当耳蜗损伤或听神经凋亡时,囊泡谷氨酸转运体表达水平出现明显改变,导致纤维投射分布的改变,产生耳鸣。
杨蓓蓓教授:耳鸣的发生机制很复杂,有多个学说,达到共识的是外周听觉受损的中枢重塑不适当的表现。临床上可见60岁以上老年人,患重度和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需行人工耳蜗植入者,极大多数伴有耳鸣症状。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后,不但听力改善,而且耳鸣症状也能获得明显改善。这就是外周听觉受损,通过中枢机制发生耳鸣的佐证。
冰丹教授:最近的研究显示,在耳鸣患者身上观察到ABR波V潜伏期延长和幅值降低,以及在功能性磁共振上发现外界声刺激诱发性反应在部分脑区降低[4]。这与笔者此前的动物研究结果相吻合,但是与很多既往文献认为的耳鸣与大脑中的过度兴奋和自发放电活动增加有关是有所出入的。这种差异性,可能与耳鸣存在不同亚型有关,也可能与部分耳鸣研究当中混杂了听觉过敏的影响有关(因为合并听觉过敏的耳鸣患者确实会表现出与单纯耳鸣患者相反的中枢反应),又或者这种中枢增益增高其实只是单纯对于听力损失的补偿,而与耳鸣无关。对于在耳鸣患者或动物身上发现的中枢反应性降低的现象,其机制解释是,在所有与IHC相连接的传入神经纤维中,高阈值低自发放电率(spiking rate,SR)听神经纤维约占40%,而另一种类型——低阈值高SR纤维约占60%[5],高阈值低SR纤维的选择性损失可触发响度异常性疾病如听觉过敏[6-8],而低阈值高SR纤维的选择性损失则认为与耳鸣有关[8-10]。高SR纤维的损失会减少听觉特异性回路中抑制性网络的驱动,引发耳鸣。而高SR纤维(亦即快速听觉纤维)的成熟和抑制性中间神经元微环路在出生后的头几个月成熟,根据这一理论,耳鸣的出现必须依赖于听觉体验的成熟。这能很好地解释耳鸣在先天性聋中发生率低但在后天性聋中发生率高这一现象。同时,临床上也发现,植入电子耳蜗可以抑制耳鸣,这可能与电子耳蜗开机后对听觉神经的电刺激通过启动高SR纤维的活动来重建快速听觉处理的关键中枢功能有关。
刘宏建教授:外周听觉系统损伤可能是耳鸣的起因,外周听觉损伤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发生结构和功能重组,产生可塑性改变从而使耳鸣持续存在。腹侧纹状体的伏隔核(NAc)和腹侧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参与了丘脑水平上耳鸣信号的消除,正是边缘区域未能阻止这一信号,才导致耳鸣感觉变成慢性的。
王慧教授:外周听觉系统的损伤是耳鸣发生的一个诱发因素,但不足以引起耳鸣的感知。在正常情况下,听觉通路异常增高的信号能够被大脑门控系统打断并限制其扩展,从而阻断其传至听皮层或者防止其被大脑有意识地感知,即“门控”机制;而当“门控”作用调控异常或者缺失时,这些信号会传播至更高级中枢,导致耳鸣的感知。耳鸣的发生伴随相应的中枢活动,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听觉相关皮层(BA20,BA21)和旁海马(BA36)等脑区与耳鸣的发生密切相关,非听皮层参与了耳鸣的发生,对耳鸣起着“门控”或者“噪声消除”的作用。耳鸣侧别与兴趣脑区侧别及其变化无明显相关,部分耳鸣患者耳鸣发生后兴趣脑区存在动态变化,高密度脑电溯源分析技术有助于判断耳鸣的起源,同时,高密度脑电溯源分析靶向定位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耳鸣具有明显的优势。
点评:
余力生教授:目前认为,耳鸣的产生是因为耳蜗病变造成的外周听觉系统活性减少时,中枢皮层的抑制功能下调,引起中枢听觉系统包括各级听觉皮层过度兴奋及神经同步化,初级听皮层频率空间排列紊乱,受损频率周围频率神经元电活动增强。目前普遍认为尽管耳蜗异常可能是耳鸣的最初启动因素,但其后中枢系统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才是耳鸣持续存在的原因,此过程也称为听觉中枢的重塑过程,由此有观点认为耳鸣属于“中枢重塑性疾病”。和杨蓓蓓主任、王方园主任达成共识。
耳蜗病变导致的听力损失引起中枢重塑,但听力损失和耳鸣之间的关系绝非简单直接,临床中相同听力损失的患者耳鸣情况不同,相同耳鸣程度的患者听力情况各异。另外,动物实验证实,噪声暴露后暂时性阈移的动物,即使听力完全恢复,听神经也会出现进展性的损伤,和相同年龄无噪声暴露者相比,螺旋神经节细胞在一年后仍有退化,那么中枢重塑的过程会一直存在,但临床中噪声暴露后出现暂时性阈移的患者,脱离噪声后听力恢复,耳鸣也会逐渐消失,即中枢神经系统重塑过程中虽都会产生过度电信号,但并非所有电信号都被感知为耳鸣。重塑过程产生的耳鸣信号是否被感知为耳鸣,还有另外系统参与,即“耳鸣管控系统”,从这个角度同意刘宏建主任及王慧主任的意见。
王秋菊教授:耳鸣的产生与外周和中枢因素密切相关,尤其是对于慢性耳鸣或者是慢性化的耳鸣,其中枢重塑异常和管控失调目前认为是主要病理机制,上述各位专家均进行了详实的解析。针对急性耳鸣的发病机制,建议要侧重于发现和鉴别耳鸣产生的可能诱因,可能的环境因素,相关的耳鼻咽喉疾病、免疫疾病、颅脑疾病、内分泌及心血管疾病,评估精神状态,睡眠质量,心理因素等,在急性期给予准确的对症治疗,有望取得较好效果。
李明教授:同意以上几位耳鸣专家的意见和余教授的点评。在我们的动物实验和脑功能研究中耳鸣的产生机制非常复杂,无法从单一结果去解释耳鸣的临床现象,且多因素造成的结果,导致我们在讨论时不能用一种视角或一种实验方法结果去笼统解释,而是需要联合各种研究结果接近临床事实,从而进行推理或建立学说。
总结:①主观性耳鸣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外周病变启动,中枢参与,可能和中枢听觉系统过度兴奋有关,单纯外周病变难以解释耳鸣。但脑功能研究显示耳鸣机制非常复杂,需要深入研究。②启动中枢听觉系统过度兴奋的病因则是多方面、多系统的,不仅仅局限在听觉系统病变,可能的环境因素,相关的耳鼻咽喉疾病、免疫疾病、颅脑疾病、内分泌及心血管疾病,评估精神状态,睡眠质量,心理因素等需要全身的视角寻找耳鸣的病因。
4. 耳鸣相关高危因素
刘宏建教授:耳鸣相关的生理因素很多,包括以下方面:①耳鸣的中枢管控系统:耳鸣和中枢敏化、睡眠、焦虑、抑郁和情绪及认知功能。②耳鸣的咽鼓管释放系统:耳鸣和胃食管酸反流、鼻部疾病和咽部疾病。③影响耳鸣的全身系统:耳鸣和更年期、饮食、肥胖、甲亢、糖尿病、高血压。④耳鸣和听力。⑤体觉性耳鸣。
宋勇莉教授:头痛和耳鸣都是常见的临床症状,二者有相似的临床特征,包括均为主观症状,均可影响睡眠和情绪,同时也受睡眠、情绪、遗传及环境因素的影响。动物实验证实三叉神经传入可与耳蜗背侧核相互作用,导致中枢听觉通路激活和耳鸣感知;同时耳鸣的产生除可导致听觉中枢的变化外,其他涉及包括注意力、情绪及记忆的大脑核团也发生改变,这与疼痛造成的大脑皮层网络的改变相似;此外还发现,头痛与耳鸣具有相似的特异性丘脑皮层活性改变,即丘脑皮层节律失常,因此推测二者可能存在共同的病理生理机制。
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偏头痛及非偏头痛型头痛患者耳鸣患病率显著高于非头痛患者,可能是耳鸣的危险因素。我们对361例主观性耳鸣患者进行调查发现,140例(38.78%)合并头痛,其中女性合并头痛比例(55.12%)显著高于男性(26.34%),以偏头痛和紧张性头痛最常见;且中-重度耳鸣患者合并头痛的比例(48.42%)显著高于轻度耳鸣患者(28.07%);头痛组患者合并听觉过敏、头晕/眩晕、焦虑、抑郁及睡眠障碍的比例显著高于无头痛组(P < 0.05),与文献报道一致。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耳鸣与头痛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这些结果均提示头痛与耳鸣具有相关性。因此,建议在耳鸣患者诊疗中常规进行头痛筛查。同时,进一步开展头痛与耳鸣的基础及临床研究,有利于阐明二者相关的病理生理机制,进而为头痛治疗在主观性耳鸣治疗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刘晖教授:耳鸣病因复杂、发病机制不明确,造成了耳鸣治疗的困境。近年来耳鸣与咽喉反流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课题组对此进行了相关临床研究:①对540例咽喉反流患者进行耳鸣调查,其中有耳鸣者309例,咽喉反流患者中耳鸣的发病率为57.22%;普通组300例,其中有耳鸣者72例,发病率为24.0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反流人群中耳鸣的发生率更高。②540例咽喉反流患者中,女性330例,发生耳鸣者203例,耳鸣发生率为61.52%;男性210例,发生耳鸣者106例,耳鸣发生率为50.48%,男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耳鸣在不同性别的咽喉反流患者中存在差异。③540例反流患者中, < 35岁者84例,耳鸣11例,耳鸣发生率为13.10%;35~55岁者250例,耳鸣123例,耳鸣发生率为49.20%;>55岁者206例,耳鸣175例,耳鸣发生率达84.95%,行卡方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耳鸣在不同年龄段人群中存在明显差异。④咽喉反流伴耳鸣患者中耳鸣的严重程度与反流症状分值具有相关性,反流症状评分越高,耳鸣对患者的困扰越大。⑤对于咽喉反流伴耳鸣患者,抑酸治疗对耳鸣症状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2个月疗程较1个月效果更为显著。⑥咽喉反流伴耳鸣患者抑酸治疗的疗效在不同性别间无明显差异,不同年龄段的疗效亦无明显差异。目前考虑耳鸣与咽喉反流关系较为密切,可能的机制分为外周和中枢两种。外周机制是咽喉反流可以引起患者咽鼓管表面活性物质减少,引起咽鼓管功能障碍,导致耳闷耳鸣;中枢机制是咽喉反流通过脑肠轴、情绪及睡眠系统对耳鸣产生的中枢系统发生负性作用,导致中央门控系统障碍,进而产生耳鸣。我们课题组初步探讨了耳鸣与咽喉反流之间的相关性,为耳鸣的诊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为进一步的相关理论机制提供了一定研究基础。
点评:
余力生教授:疾病分为简单疾病与复杂疾病。简单疾病如耳石症,不管病因如何,手法复位有满意疗效。而复杂疾病如慢性耳鸣,常为多病因,只用一种手段处理其中一个因素,如果找到的是最主要的致病因素,疗效或许尚可,如果是非主要因素,则疗效欠佳。这也是耳鸣异质性很大的原因之一。看待耳鸣的视角,从听觉系统扩展到耳鸣管控系统,包括中枢耳鸣清除系统及咽鼓管系统,影响这些系统的生理因素都可能对耳鸣的发生产生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生理因素和耳鸣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头痛,并不是所有头痛患者都有耳鸣,只有高危因素累积,达到一定的诱发耳鸣出现的阈值,才会引起耳鸣。耳鸣的治疗中要有多病因观念,大多数疾病的发生不是因为单一事件或者单一结构的损害引起,都是由同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引起,多种因素常常在同一时间出现才能引起疾病的症状和体征,耳鸣更是如此。耳鸣的代偿系统中很多因素一般人群发病率很高,女性偏头痛可以达到17%,喉咽反流人群的发病率也可以达到10%以上,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在更年期妇女中很常见,随着肥胖的增加,OSA的发病率逐渐增高,因此同一患者中同时存在多种影响因素比较常见,如何找到最大权重又能给予干预的病因是耳鸣治疗中最困难的一点。
王秋菊教授:生理因素是导致耳鸣的重要因素之一。耳鸣的出现正是提示患者的体内生理指标或指征异常的一个提前的信号。因此,对于存在上述各位专家提出的各种异常生理现象或者高危生理指标的人群,耳鸣的产生往往是一个早期的良性警示:提示患者要调整好睡眠(时间够、深度够、醒后头脑清醒),处理焦虑或抑郁的状态(药物调节、心理调节),检查有无胃食管酸反流、鼻部深在疾病、咽部疾病等,更要注意有无颅脑疾病、恶性肿瘤等,要注意调节血糖、血压、血脂和饮食,减少更年期症状,给予适度的纠正和治疗,要进行专科检查,了解听觉传导通路是否正常。当然,所有的诊断和判断是要分层、分级的,有的需要问诊解决,有的需要专科检查来回答,有的需要多学科会诊(MDT)来处理,同时耐心的解释与沟通、对患者的教育、针对性的药物也是需要的。
李明教授:采用耳鸣相关高危因素描述是相对比较准确的一个词汇。提示这些因素如头痛、鼻部疾病、激素水平、OSA等,虽然和耳鸣相关,但与耳鸣的发生之间绝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虽然宋勇莉教授和刘晖教授的数据证实头痛及反流人群中耳鸣的发生率较高,但不是所有的头痛和反流患者均有耳鸣。正如余教授所言,耳鸣是多病因的复杂疾病,是多种因素累积达到发病阈值而出现的,是量变到质变的关系,所以用耳鸣相关高危因素来表述比较准确。还应该说明的是这些可能病因不是耳鸣起因的主流,是中国学者新近发现的,对耳鸣病因的补充。
总结:①除了听觉系统内的相关病因,越来越多的其他生理因素可能和耳鸣的发生有关,比如更年期激素水平变化、OSA、头痛尤其是偏头痛、咽喉反流等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和耳鸣之间存在绝对因果关系,耳鸣是多种因素累积发病。②耳鸣虽为多种因素累积发病,治疗中可能不需要去除全部因素(目前看这也是不可能的),只需要改善可以改善的因素,将累积效应降至耳鸣发病阈值以下,可能会使部分耳鸣消失,尤其是急性耳鸣和慢性代偿性耳鸣。③慢性失代偿性耳鸣,对伴随症状的处理较耳鸣本身更加重要,此次圆桌论坛没有涉及这部分内容,希望有机会后续专题讨论。
5. 耳鸣的治疗—正面咨询
高下教授:耳鸣是耳科门诊常见的主诉之一。患者就诊时间多在发病的一周左右(急性期)和一年左右(慢性期)。相当一部分急性期患者就诊是担心自己得了大病,心理恐惧;慢性期患者就诊,是觉得耳鸣影响睡眠、工作、生活和心情等。我们鼓励耳鸣患者及时就诊,在排除器质性问题之后,主要是让特发性耳鸣患者理解并接受耳鸣只是一个症状,并不是一种疾病,耳鸣本身对患者无生命危险,耳鸣应该是一种“吹哨人“的角色。接诊医生要减少、最好消除患者对耳鸣本身的恐惧,鼓励患者利用“吹哨人”调整作息、心情等,从而更利于身心健康。慢性特发性耳鸣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应该是认知行为治疗,包括放松训练、认知重建、注意力转移、意象训练和困难缓解训练等。其中认知重建最为重要,我们门诊时间有限,让患者建立起对自己耳鸣的正确认识,耳鸣也就好了大半。中医药对慢性特发性耳鸣也有一定的疗效,尤其是艾灸联合针灸。耳鸣患者容易伴有心理问题,我们要在治疗的过程中及时纠正患者进入认识的误区,追踪患者的问题点,给患者更多的针对性建议。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耳鸣残障量表、匹茨堡睡眠量表以及焦虑和抑郁量表,找出患者的诱发因素,指出是患者的心理问题或者睡眠问题引发了耳鸣,而不是耳鸣造成心理问题或者睡眠障碍。
俞艳萍教授:耳鸣是耳鼻咽喉科门诊常见的主诉。作为耳科大夫,我们需要通过详细的问诊、仔细的查体、适当的辅助检查甚至MDT来寻找耳鸣的病因,从而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对于病因明确的继发性耳鸣,通过积极治疗原发病,耳鸣会得到缓解甚至消失;而无法找到明确病因的特发性耳鸣,需要根据不同阶段不同类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在与耳鸣患者的交流中,我感觉很多患者是因为对耳鸣不了解,担心会有严重的情况发生而心存恐惧,故而显得焦虑不安。所以我一直试图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耳鸣的发生,比如用“过载理论”解释不伴有听力下降的急性耳鸣,用“补偿理论”解释亚急性及慢性耳鸣,用“影子理论”解释代偿性特发性耳鸣。特发性耳鸣的转归,我认为都会趋于好转。耳鸣就像一个伤口,刚出现时觉得它很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注意力会转移,耳鸣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慢慢变小,我们要相信大脑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接触越多的耳鸣患者,对“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句话的体会越深。患者因为不了解而恐慌、焦虑,需要我们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去多多解释,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早日走出被耳鸣控制的生活。
宋纪军教授:原发性耳鸣,特别是慢性耳鸣患者,一定是多病因的,其背后有复杂的机制参与其中,耳鸣也一定不仅仅由耳部疾病引起。怎样重新认识耳鸣,就如同“盲人摸象”启示我们,不能把局部当整体,一定要有疾病的整体观。我们在临床中常常发现,有许多耳鸣患者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有些可能就是“病因”。不良的生活习惯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导致人体脏腑功能失调,使人体出现亚健康状态,从而引起“耳鸣”等症状的发生。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个人健康与寿命,60%取决于生活方式,环境因素只占17%,遗传生物学仅占15%,而医疗卫生状况才占8%,由此可见健康的生活方式多么重要。不仅如此,生活方式已经提升到“生活方式医学”时代,其概念就是通过对生活方式的循证医学改良,以非药物、非手术的方式达到慢性疾病的预防、逆转与康复。
加强患者教育非常重要。医师要发挥好“师”道的作用—“传道、授业、解惑”;教育患者要调整不良的生活方式,正确认识耳鸣的诱发因素,消除对耳鸣的认知困惑,要知行合一;让患者了解耳鸣是人体发出的“善意的警铃”;要让患者明白,自己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一切的根源都在自己,想真正改变“耳鸣”,首先要改变自己的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你变了,一切才能改变,你变了,你就会离“耳鸣”越来越远。
点评:
余力生教授: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对未来不可控的负性事件产生的恐惧。所以,首诊医生如果只告诉病人这是神经性耳鸣,终身都好不了,就会加重耳鸣患者的恐惧,诱发焦虑/抑郁。其实人的大脑有很强大的消除功能,没有意义的信息会被逐渐清除。如果患者总是在关注耳鸣的情况,这条网络通路就会不断强化,导致消除困难。所以,在几乎所有的耳鸣指南中,都将正面咨询和耳鸣的认知行为治疗作为强烈推荐方案,与慢性耳鸣发生中恐惧反应、灾难化想法有关,从而导致耳鸣这一报警功能过度敏感。降低敏感度、改变认知非常重要。但要注意,指南针对的都是慢性耳鸣,尤其是慢性失代偿耳鸣。但是正如前面所讲,急性耳鸣和慢性耳鸣不同,急性耳鸣事出必有因,多由某些生理因素引发,我们耳鼻喉医生是面对急性耳鸣的一线医生,在处理急性耳鸣时,积极寻找引起这次急性耳鸣的生理因素,尽量消除耳鸣是第一目的。目前国际上尚未有急性耳鸣的共识,建议从规范急性耳鸣的治疗开始,如果能把急性耳鸣处理好,就会大大降低慢性耳鸣的发生率。
王秋菊教授:非常同意余力生教授针对急、慢性耳鸣的不同处理原则的观点,我也在前面的观点中表达了我的想法,急性耳鸣和慢性耳鸣的发病机制是不同的,诊断思路和处理原则也应不同。我也很认可高下教授、俞艳萍教授对耳鸣患者进行通俗易懂的宣教和积极的咨询及干预治疗的观点。当我们对一个耳鸣患者进行了详实的分析、明确的诊断、排除其危险性疾病事件后,需要做的就是针对其心理、精神、睡眠、焦虑、听力等各个事件进行逐一的干预,而有效的干预和帮助,会使其从高等级的耳鸣困扰逐渐进入低等级的耳鸣状态,临床上就可以看到效果,因此,医生对患者耳鸣的判断和分析,采取的积极应对的态度以及表达的清晰准确的语言也会影响患者的疗效。
李明教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在临床上却是耳鸣患者最需要得到的支持和帮助。但在临床就医中患者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运气,因为大多数患者因耳鸣就医时很难找到耳鸣医生,同时由于现在网络的发达耳鸣患者得到的大多是负面信息,加上大多数非耳科医生还不太了解耳鸣治疗的进步,常常简单回复耳鸣是世界难题,治不了、治不好,可以直接加重患者病情。所以起病时没有得到正面咨询,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也是亟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如何解决?耳鸣诊疗科普宣传是主要选项,耳鸣诊疗的继续教育对我们医生显得尤为重要,建议各级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的领导在每次年会召开时,增加有关耳鸣诊疗进展的介绍,使更多医生了解、熟悉和掌握现阶段耳鸣是可以治好但较难治愈的现状,以造福耳鸣患者。
总结:①耳鸣患者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各国指南均作为强烈推荐治疗,不仅可以减少急性耳鸣慢性化,而且可以减少慢性失代偿耳鸣的比例。②如何进行正面咨询,关键在于将耳鸣的合理性和警铃作用传递给患者,和患者一起寻找耳鸣背后的病因,除外恶性病因的前提下,推荐进行生活方式调整,调控耳鸣高危因素,而不是过度注意耳鸣本身。
6. 耳鸣的治疗—药物治疗
张剑宁教授:随着耳鸣规范化诊疗理念的普及,近年来国内同行对耳鸣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已普遍认识到耳鸣不是一个简单的临床症状,仅靠1~2种药物或方法就能解决耳鸣存在的所有问题,甚至消除耳鸣,是一种错误观念。耳鸣综合疗法2.0版体现了目前对耳鸣的全新认识,普遍适用于各种类型和程度的耳鸣,可针对性地制定方案,规范诊疗。现针对患者不同治疗目的,解析耳鸣综合疗法2.0版的应用。①如果患者治疗的目标仅仅是了解耳鸣的原因或危害,往往表明耳鸣并未对患者造成较大的影响,在一般耳鸣检查基础上的交流解惑往往可以解决多数患者的问题。这类患者无需过多干预。②如果患者希望耳鸣声减轻,减少对生活的影响,说明耳鸣已经对患者造成困扰,则需要在交流解惑的基础上,评估患者在睡眠、躯体障碍方面存在的问题,给予患者最适合的声治疗模式及适当的对症治疗。这些措施不应过于繁杂,不会给患者的正常工作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③如果患者存在减轻或消除耳鸣的强烈愿望,往往提示其对耳鸣认知出现较大的偏差,耳鸣带来了较大的困扰。此时应对患者进行仔细和全面的听力学和耳鸣严重程度评估,以及认知、睡眠和心理障碍的评估。这类患者往往耳鸣程度较重,需要在交流解惑、特殊声治疗的基础上,采取较为全面的对症治疗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患者睡眠、情绪及认知等方面的干预,依据患者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综合诊疗措施。耳鸣综合疗法2.0的正确应用,将是临床上科学、快速、有效干预耳鸣的途径和基础。
曾祥丽教授:耳鸣发生后,患者的感受分为两个层面:对耳鸣的感知和对耳鸣的反馈。耳蜗损伤后,患者感知到耳鸣,常常描述耳鸣类似铃声、打字声等大自然的各种声音,一部分患者并不介意,一部分患者会积极寻求医生帮助,一旦医生告知耳鸣发生的原委并排除危险因素后,患者便不再介意,并且可遵循医生的治疗及预防指导;然而,另有一部分患者,因为耳鸣带来的不适感,加之来自网络的不当宣传,逐渐对耳鸣产生厌恶、恐惧,继而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基于此,耳鸣的药物治疗也分别针对耳鸣的感知和耳鸣的负面反馈。
在听力损伤的急性期,积极实施挽救听力的治疗,当听力恢复正常后,耳鸣可随之消失,这部分治疗用药参照突发特发性聋的治疗。对于慢性耳鸣,基于动物实验发现,耳蜗损伤后听觉神经重复高频率放电,中枢的下行抑制调控减弱,因此借鉴癫痫的治疗药物获得一定疗效,其中卡马西平为代表性药物。但是,个别患者可能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包括剥脱性皮炎。为安全起见,建议使用前检测HLA-B*1502基因,阴性者可试用。利多卡因静脉滴注治疗耳鸣也很早见于文献,住院患者在心电监护下可以安全使用,有心脏病/传导阻滞患者慎用。值得注意的是,耳鸣患者异质性很强,这些方法并非对所有患者有效。
针对耳鸣的负面反馈,经过精确的评估确认存在焦虑、抑郁、睡眠障碍者,可以通过相应的药物减轻不良反馈,如阿普唑仑、氯硝西泮、舍曲林,小剂量开始,根据病情逐步增加剂量,通常两周左右可以让患者感觉到耳鸣困扰减轻,从而增加后续治疗的顺从性和信心。
刘宏建教授:并没有针对耳鸣本身的药物,但是可以针对引起耳鸣的原因进行治疗,包括:耳源性参考突聋的治疗;中枢性调整情绪睡眠药物,音乐疗法,经颅磁电刺激等;全身因素:对甲亢、糖尿病、高血压血脂等的治疗;减肥和适当运动;咽鼓管相关疾病处理:鼻炎、咽炎、胃食管反流、咽鼓管异常开放。伴有体觉性耳鸣的患者可以给予:①物理治疗:包括手法治疗(扳法、颈部肌肉松解法、整脊法);②药物治疗:非甾体抗炎药,抗癫痫药物及三环类等抗抑郁药物,盐酸乙哌立松,加巴喷丁。
左汶奇教授:临床耳鸣人群数量庞大,且大多数耳鸣并不能明确具体发病原因,这给治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其中言语频率听阈正常而伴耳鸣患者并不少见,在排除器质性病变后,即使在急性期(小于3个月)内耳鸣治疗效果仍欠佳,为此我们在排除新发生的突发性聋患者后,将病例分为两组,即急性-亚急性耳鸣组77例(小于6个月)和慢性耳鸣组70例(大于6个月)。治疗方案:口服金纳多(每次1~2片,每天2~3次)的同时,耳后注射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液,注射频率为半个月一次,总计3~5次,注射前后完成纯音+声导抗、耳鸣匹配、ABR检测及耳鸣评分和THI量表,治疗后15 d、1个月、2个月、3个月随访(随访内容同前)。数据经卡方检验和t检验分析后,结果显示急性-亚急性耳鸣组总体有效率明显高于慢性耳鸣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在治疗前后的THI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干预治疗疗效确切,急性-亚急性耳鸣组较慢性耳鸣组疗效更好,耳后注射复方倍它米松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尤其是对急性-亚急性耳鸣组。
点评:
余力生教授:根据耳鸣的机制,属于中枢系统过度兴奋,给予一定的药物可能有效,但是现阶段还不能预测哪些患者有效,哪些无效。可以这样说,急性耳鸣是症状,背后的病因千差万别,寻找不同的病因给予不同的药物治疗应该可以解决,只是有些因素干预起来非常困难,比如外伤和年龄,有些因素干预起来不能去根,比如头痛和反流,反复发作会诱发耳鸣的反复加重。慢性代偿性耳鸣因为没有情绪系统过度参与,治疗和急性耳鸣类似,主要寻找生理因素;但是慢性失代偿性耳鸣,则主要修理耳鸣这个报警器,不要过度敏感,这部分确实认知行为治疗比较重要。
理解了以上有关耳鸣的观念,耳鸣的诊治也就有了原则可循。实现前庭代偿的前提是:中枢必须有足够的功能,外周病变必须稳定,两者缺一不可,耳鸣代偿也应该需要类似条件:其一是听觉中枢必须有足够的功能,其二外周(包括听觉系统和听觉系统周围系统:咽鼓管、颈椎、颞颌关节等)必须保持稳定状态。所以面对急性听觉系统损伤(比如突聋),要努力提高听力,力求去除耳鸣的启动因素,听力不能恢复的,也可以采用助听装置尽量弥补听力损失(助听器、声治疗、人工耳蜗等),虽然这些听力损失不一定是耳鸣的直接原因,但肯定是耳鸣的参与因素之一,在寻找不到其他系统病变的情况下,弥补听力损失对患者没有任何弊处。其次,也要积极寻找其他系统病变,包括耳鸣的阿控门代偿系统,以及咽鼓管系统病变,尤其对于双侧对称的稳定听力损失的耳鸣患者尤为重要。
必须强调的是,耳鸣绝大部分是良性信号,但是也有少部分是危险信号。寻找病因最主要的是除外危险的病因,如听神经瘤、鼻咽癌、颅内各种病变等。对于单侧伴有听力下降的耳鸣,必须做MRI检查,以除外桥小脑角占位性病变。
虽然耳鸣的病因众多,查找困难,但是只要认真分析,大部分慢性耳鸣的病因是可以找到的,只要找到病因,疗效就会大大提高。而在寻找耳鸣病因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整体医学观,虽然耳鸣表现在耳部,但是病因大部分在全身,这是耳鸣诊疗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王秋菊教授:从上述详实的耳鸣治疗讨论中可以看到耳鸣的治疗具有复杂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系统的诊断思维和有效的判断在耳鸣治疗中尤为重要。在临床实践中,诊治耳鸣患者,首先是帮助她/他排除危险因素,之后是要高度关注患耳鸣的这个人,她/他的主诉,她/他的困扰,她/他的目标,她/他的期望值以及她/他的最为关切和痛苦的点,抓住主要矛盾,逐一去除病症,帮助她/他从耳鸣患者转变为耳鸣人群或者是有过耳鸣经历的人群。
李明教授:绝大多数药物都有靶向,而耳鸣还无法被靶向。但是目前基本共识是,急性期可以参照突聋方案进行治疗,我喜欢在用激素的剂量上根据患者年龄适当打7~8折,算是自我安慰。而对于亚急性或慢性耳鸣患者,我们只对耳鸣继发的临床症状进行用药,可以较快消除失眠、心烦和焦虑等症状,帮助患者提高依从性,达到缩短适应耳鸣的时间和患者诊疗期间的良好体验。因此,目前国内就耳鸣药物治疗问题已经明确,重点在于消除耳鸣诱发的不良心理反应和躯体症状而不是耳鸣本身。
总结:①各国指南对于慢性原发性耳鸣不主张药物治疗,其原因是病因不明,用药往往缺乏针对性。②目前尚没有一种普遍适用于所有耳鸣的有效药物,但并不说明药物无效,而是耳鸣病因众多、复杂,异质性很强,如果能仔细查找病因,进行相关机制分析和细化分类,找到更能针对每个不同个体病因的药物,方有望取得更好疗效。某些药物对某些类型耳鸣可能会有很好的效果,这也是以后的研究方向。③现阶段针对耳鸣的药物可以分为2类,一类是针对耳鸣本身,另一类是针对耳鸣伴发的焦虑、抑郁、失眠等症状。一般情况下,后者是前者有效的前提。在给予患者治疗时,要分清治疗目的,评估效果时也要有所不同。④现阶段急性耳鸣可尝试突聋方案,比如金纳多、激素,部分患者也可取得很好疗效。要注意部分敏感患者可能兴奋欣快,影响睡眠,可酌情减量使用。
7. 特殊人群耳鸣
张劲教授:谈一下对儿童耳鸣的认识。先天性聋患者很少有耳鸣,人类从胚胎第27周至出生后6~12个月是听觉系统发育的关键时期,耳鸣常发生于关键期后的后天性聋患儿。儿童耳鸣发生率,极重度耳聋比中度耳聋低,感音神经性聋(29.5%)比中耳疾病(43.9%)低。对756例7岁儿童的调查显示:听力正常者41%有耳鸣经历;听力损失者58%有耳鸣感觉。过度或长期噪声暴露是青少年耳鸣的主要危险因素,据报道,5768例耳鸣患者中,19岁以下儿童仅112例,14%有噪声暴露史,12%有中耳炎史,16%口腔正畸,12%颈部肌肉紧张,9%心理障碍,4%有病毒感染史。
自记事起就有“嗡嗡”耳鸣声的幼儿,会以为耳鸣是正常的,不被问起则不会主动诉说,或者以为耳内真有蜜蜂在叫,说出来别人不信,所以儿童耳鸣从发生到就诊常在一年之后。儿童比成人更易适应耳鸣,随着年龄增加,恼人的耳鸣随之增加,尤其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慢性耳鸣发生率为4.7%),耳鸣还常同时伴有听觉过敏(约占38%)。儿童耳鸣的困扰主要是睡眠困难,注意力不集中且易受干扰,影响学习,易出现焦虑和抑郁。严重的耳鸣困扰如不及时干预,将会影响其一生,所以儿童青少年耳鸣要针对主观性恼人的耳鸣进行及时干预,有效的方法是行为认知疗法,辅以声治疗、注意力控制技术和放松训练。
儿童耳鸣没有标准化的问题问卷。儿童耳鸣的问诊,以父母提示或闭合式的问题先引导切入主题,接着提出更多开放式的问题,由孩子诉说耳鸣的经历,他们的担忧和对其原因的解释会更真实,耐心听取他们自己想出对他们有用的解决方案时,是最有效的。
点评:
余力生教授:儿童耳鸣虽不常见,但也会遇到。儿童大脑处于发育阶段,脑供血可高达全身血供的50%(成人一般在20%~25%),如果再给予强刺激,如长时间看电子产品(手机、电子游戏),吃兴奋类的饮食,就会使大脑兴奋度过高,这是儿童特发性耳鸣最常见的病因/诱因之一。
王秋菊教授:儿童耳鸣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耳鸣儿童,其听力往往超好,听力在零分贝或负分贝范围,DPOAE也显示出极好的反应,性格相对安静或孤僻,有时要鉴别患儿是否存在孤独症。另有些儿童耳鸣是他觉性耳鸣,可以清晰地听到耳内肌痉挛的声音,往往未给予干预和治疗也能适应,并不烦躁。突聋患儿亦有耳鸣,但往往与成人不同,代偿重塑较早,困扰较少,随着听力的好转,耳鸣恢复的也较快。
李明教授:关于儿童耳鸣我的意见很明确,在我的耳鸣专病门诊一年也看不到几个耳鸣患儿(个位数)。①坚决不做流调(发现了又怎么样?在没有有效治疗手段前,可以让它处于完全适应状态自由存在)。②除非儿童自述有耳鸣我们才给她/他作全身及听力学系统检查,除外耳聋或占位性病变的危险因素,否则家长会比孩子更紧张焦虑,每天有事没事去询问有没有耳鸣?声音大小?从而使儿童过多关注耳鸣而逐渐变成耳鸣患者。这是我们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坏结果。③治疗上成人可以出现适应,儿童也会适应,但要付出更多才会得到这个结果。
总结:儿童耳鸣有其特殊性,首先主诉可能不清,其次对耳鸣更容易适应,在排除明确病因和可能的恶性疾病基础上,给与患儿及家属正面咨询解释更重要。
杨仕明教授总结:耳鸣是越来越值得关注的耳科难题,虽然确实有很多谜题,但通过此次圆桌论坛,耳鸣相关的概念、发病机制、可能的高危因素、治疗策略还是可以达到共识,下一步需要研究的方向也进行了梳理。虽然耳鸣的发病机制比较公认是中枢代偿性反应,但是具体反应模式需要进一步研究,耳鸣高危因素逐渐从耳部疾病扩展至全身因素,如何认识这些高危因素在耳鸣发生中的作用和权重,以及针对治疗对耳鸣的效果,尚需大量临床研究。耳鸣的正面咨询方案,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推广,耳鸣的路还很长,全国同道携手努力。
编者按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临床诊疗技术和方法不断发展和完善。本专栏的开辟旨在创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针对本学科临床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邀请在相关领域做出大量工作并颇有建树的专家和教授,介绍他们的见解和经验,以飨读者。圆桌论坛为个人意见,不具共识性。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ferences
- 1.McCormack A, Edmondson-Jones M, Somerset S,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eporting of tinnitus prevalence and severity. Hear Res. 2016;337:70–79. doi: 10.1016/j.heares.2016.05.009.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2.余 力生, 马 鑫. 深入认识偏头痛及中枢敏化综合征. 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2021;35(2):97–100. doi: 10.13201/j.issn.2096-7993.2021.02.001.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3.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头颈学组 搏动性耳鸣影像学检查方法与路径指南. 中华医学杂志. 2013;93(33):2611–2612. doi: 10.3760/cma.j.issn.0376-2491.2013.33.002. [DOI] [Google Scholar]
- 4.Hofmeier B, Wertz J, Refat F, et al. Functional biomarkers that distinguish between tinnitus with and without hyperacusis. Clin Transl Med. 2021;11(5):e378. doi: 10.1002/ctm2.378.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5.Heinz MG, Young ED. Response growth with sound level in auditory-nerve fibers after noise-induced hearing loss. J Neurophysiol. 2004;91(2):784–795. doi: 10.1152/jn.00776.2003.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6.Hickox AE, Liberman MC. Is noise-induced cochlear neuropathy key to the generation of hyperacusis or tinnitus? J Neurophysiol. 2014;111(3):552–564. doi: 10.1152/jn.00184.2013.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7.Singer W, Zuccotti A, Jaumann M, et al. Noise-induced inner hair cell ribbon loss disturbs central arc mobilization: a novel molecular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tinnitus. Mol Neurobiol. 2013;47(1):261–279. doi: 10.1007/s12035-012-8372-8.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8.Zeng FG. An active loudness model suggesting tinnitus as increased central noise and hyperacusis as increased nonlinear gain. Hear Res. 2013;295:172–179. doi: 10.1016/j.heares.2012.05.009.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9.Rüttiger L, Singer W, Panford-Walsh R, et al. The reduced cochlear output and the failure to adapt the central auditory response causes tinnitus in noise exposed rats. PLoS One. 2013;8(3):e57247. doi: 10.1371/journal.pone.0057247.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0.Hofmeier B, Wolpert S, Aldamer ES, et al. Reduced sound-evoked and resting-state BOLD fMRI connectivity in tinnitus. Neuroimage Clin. 2018;20:637–649. doi: 10.1016/j.nicl.2018.08.029.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