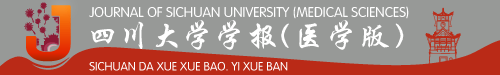Abstract
健康中国战略对医学人才的培养提出新的要求,新医科模式下的医学人才培养需要对其内蕴的复合型的法治要素进行有效回应。新医科战略实施过程中,面对医疗风险范围的拓宽、患者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医学教育的惯性逻辑,医学教育应该在早期注入法治元素,培育医者具备相适应的法律素养,以规则思维、平等思维和底线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对医疗实践中的法治难题进行有效回应。法治教育正是回应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转变和医疗法治难题解决的的路径选择,通过法治教育能够规避技术嵌入风险、规范调节医患关系以及重塑医学人文环境,从而提升新医科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Keywords: 新医科战略, 医学教育, 法治教育
Abstract
In line with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new requirements for medical education have been raised. Medical educa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 new model of medicine demands an effective response to its inherent complex elements concerning the rule of law.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medicine strategy, in face of the widening scope of medical risks, the growing awareness of patient rights, and the conventional logic of medical education, elements concerning the rule of law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so as to help medical practitioners develop the appropriate legal literacy and rely on ideas of rules, equality and ethical bottomlines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Thus, medical practitioners would be better equiped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legal problems they encounter in their medical practice. Legal education is the route of choice in response to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mode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the attempt to solve complicated problems through medicine and the rule of law. Through legal education, the risks of technology embeddedness could be avoid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ients and medical practitioners could be regulated in a standardized way, and the medical humanistic environment could be reshaped, there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new medical education.
Keywords: New medicine strategy, Medical education, Rule of law education
1. 医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是培养卓越医学人才的新路径
新医科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医学教育领域的实践,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基础[1-2]。面向未来技术和医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需求,新医科战略对医学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当前医学模式正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由治疗为主向兼具预防治疗、康养的生命健康全周期进行转变,同时人民群众期盼有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些变革催生医学教育的创新。新医科战略通过全面整合精准医学、转化医学等新兴专业,构建“新医科”教育新体系,培养适应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和以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生命科学变革,并且能够运用交叉学科知识解决未来医学领域前沿问题的高层次医学创新人才,从而实现由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的转变、向以“医文、医工、医理、医X”交叉学科支撑的医学教育新模式的转变[3-4]。新医科战略下医学人才培养通过立德树人、三全育人、以智启人、以体育人、以美成人、以劳塑人的主要路径着力,将大健康教育与全面素质教育结合,着力培养符合新时代需要的、全面发展的新医科人才[5]。
以口腔医学为例,口腔医学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类口腔领域的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防治重点,关切人类身体健康。口腔医学有以下重要特征:一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步。新材料、新设备、数字医学、显微医学、微创医学、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能医学等正改变着口腔医学的诊疗模式,成为驱动口腔医学创新发展的先导[6]。二是疾病诊治与美的重塑紧密相关。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健康意识、对美的要求日益增加,尤其是对健康口腔、靓丽容貌的要求越来越高。三是诊疗过程的精细化和反复性,医患互信合作是治疗成功的关键要素。口腔医学的三个特征,体现了医学学科与人文学科一定的关联性,紧随技术的同步,需要更好地使用技术,填补“技术理性”;诊治和医美结合,需要有效合理满足患者需求,填补“价值理性”;诊断过程的精细化和反复性,需要建立科学、合理和有效的治疗模式,填补“规范理性”。而法学学科作为人文学科中的基础性学科,能够通过规则思维、平等思维和底线思维加持医学人才的专业素养,并顺应习近平总书记“法治中国”建设构图的全域化落实。结合新医科战略对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要求,通过医学与人文学科尤其是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在夯实医学专业基础和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加强医学生的法律素养、人文素养等教育,是新医科战略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新内涵,更是培养卓越医学人才的新路径。
2. 新医科战略下医学人才培养面临的法治环境
2.1. 智能技术拓宽传统医疗风险的范围,带来应对新医疗风险的难题
新医科战略是为了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传统医学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进行融合的交叉性战略。智能技术的嵌入会带来医疗水平的提升,有效快捷解决医疗难题,但“智能+”这种模式现实中更多是以回应事项需求为导向,这种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虚拟性[7],拓宽了传统医疗风险的范围,给新医科战略实施带来挑战。
一是智能技术带来隐私风险应对的难题。传统医学中,医者对于患者的信息的掌握是进行医疗手段的前提,严守患者的个人信息是医务工作者的纪律准则。在智能技术大量引入之后,医者多数扮演操作、指令甚至整理相关信息的角色。患者信息的获取、储存和利用等多个过程,依循技术路径存现于智能技术的场域中,并依据既定的程序和步骤进行汇集,相关信息的安全显然不仅需要医者职业约束来确保,还需要技术本身的可靠、运行的规范等来确保,这就将主体带来的风险隐忧进行多个环节的嵌合,隐私风险的可能性也就在多个节点衍生。二是智能技术带来舆情风险应对的难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智能社会是信息社会的高级形态[8],信息的可控性、韧性和缓冲性较之以往有着显著差异,这就容易导致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层层加码,舆情风险也就由此而生。医疗领域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医患关系的舆情风险,互联网、大数据等媒介对于相关信息的传播缺乏筛选和过滤,在由网络技术建构的传播链上,技术给相关信息附加的直接性、瞬时性以及聚合性,导致民众极易被误导,从而形成社会舆论反过来给医者施加压力。
2.2. 患者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带来患者诉求需要医者有效回应的难题
新医科所倡导的全过程、全周期的健康理念,是对传统医疗模式的重塑。促进健康是以医者和患者间实质性的平等关系为前提,通过双方有效的沟通来进行预防手段和治疗手段的展开。当前智能技术助推医疗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患者对于疾病的期望和认知也在逐渐攀升[9],智能技术的嵌入又因自身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这种矛盾,相关隐患也就随之产生。
一是基于治疗需求,患者的医学知识得到自主性丰富,但是缺乏专业性引导。医者和患者尽管在法律地位上出于平等主体的地位,但是在疾病诊断治疗的过程中,患者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更多是由医者来进行解释和阐明,医者将医疗方案告知患者,由患者自己决定相应的治疗模式和承担相应的结果,以此来尊重患者的知情权。但当前智能社会不仅仅是医疗体系的智能,更是整个社会的智能,通过对信息的收集,患者也能够基于自身情况去补足相关的医疗知识。某些情况下,当患者所了解的信息和医者的专业判断发生冲突时,如何去有效沟通和规范解决,从而疏解紧张的医患关系,是所有医者可能会面临的挑战。二是基于技术发展,患者的治疗期望内生性增加,但是缺乏合理性预期。尽管技术的嵌入使得许多医学难题被攻克,但医学毕竟是经验性的学科,需要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充分的实践为前置要件,这就容易引起患者对疾病治愈期望的短期要求和医者对医疗技术成熟使用的长期实践的紧张关系。此外,当前医患纠纷多数由于患者对治疗结局有着高于目前医疗水平的结果期待,导致患者对医疗行为提出质疑,智能技术引入后又加剧这种评价标准的混乱,以往过错性标准在虚拟医疗中难以寻找实际的责任主体,相关行为规范的缺失又助长了这一任意性,这就需要相应的教育来提升医者的法治素养,规避“医闹”现象。
2.3. 重专业、轻人文的惯性医学教育,带来教育方式亟需转变的难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申将“加强救死扶伤的道术、心中有爱的仁术、知识扎实的学术、本领过硬的技术、方法科学的艺术的教育”作为新医科人才培育的基本原则之一[10]。但厚植医学教育本身,相较于工科、文科等其他学科,医学人才往往需要对标更强的专业性标准,但是新医科战略下,这种医学人才的培育惯性还在继续,未有效适配形势和要求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医学院校的其他学科课程体系设置不完善。以法治课程为例,当前医学院校对于医学生的法学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医学人文课程的比例和课时较之以往有了明显上升,但是多数课程的内容更侧重于医风医德的培育,尽管多数课程也是在学习宪法和法律,但是内容更多是侧重回应法治教育的形式要求,与医务人员紧密联系的相关法律法规缺少专业性的解读,法治教育的系统性、实用性也就大打折扣。二是医学生对于其他学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同样以法学学科为例,尽管医学生对职业准入标准有着清晰的认识,但是除了过硬的医疗技术、高尚的道德情操之外,缺乏对自身高度负责的法律意识。医者提升法治素养,不仅能够确保医疗活动的顺利进行,进行规范化治疗避免医疗风险,更能确保医患间的交流和沟通走向理性,从而凝聚医疗方案的共识,化解多数由医患关系带来的矛盾和阻碍。此外,传统医学注重用道德标准内化自己,通过强化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来进行自我约束,这种内生性无法全面应对技术带来的侵益性和损益性,更需要提升医者的规则意识来进行兜底性应对。
3. 新医科战略蕴含的新医学人才培养的法治要素
新医科建设是适应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质量革命需要提出的创新举措[11],新医科的本质是创新,是内涵、形式、外延等多重意涵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12];新医科探索的是医学内部学科专业、医科+工科以及医科+文科[13]等复合教育模式,以此回应新医科学科交叉、融合创新人才培育理念[14];新医科战略的实施对医学教育的规模、培育模式、培训载体等提出新的挑战,这也是新医科战略落地的着力点[15-17]。尽管现有研究从多个维度去解读新医科战略对于医科人才培育的作用,但是缺乏寻差性的视角去界定医科专业的独有属性,对医学人才的培育也未在医者和患者这一二元关系的范畴之内溯源。
部署实施新医科战略的系列文件中内蕴着卓越医生的素质要求,这也是医科人才培育的目标。在“健康中国”战略对卓越医学人才需求的背景下,以核心胜任力为教学导向、全周期为专业结构以及注重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等理念中,折射出复合型的人才标准,即需要具备复合性的知识和能力来应对复杂的具体事务。新医科战略下,医学领域的风险不再仅仅限定于医科范畴,而是依循医疗技术建立的工具化、机械化路径,跨越传统医疗风险的界限,与其他领域的风险交织和复合。如医患纠纷往往会涉及法律层面甚至意识形态等层面,这就需要医科人才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水平来应对。复合型人才的要素,为新医科人才的培育指明方向,但同时这种要素也为法治教育融入医科教育提供了空间和媒介,而法治教育对于上述要素的建构显然也是正相关的促进作用。
具体而言,新医科战略中医学人才培育的复合性要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知识结构要顺应学科交叉的复合。对于学科而言,新医科战略实施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应对智能技术带来的科技革命,这就产生一定程度涵盖相关学科的需求——需要扩容原有医学学科的边界,对涉及的其他学科要素进行理论的有效补足和持续供给;对于医科人才培养而言,这就要求新医科人才需要拥有全方位复合型的知识结构[18],需要在医学实践中培养进行多学科观察和思考的能力,需要应对医疗主体产生的但不限于“医”的事务和情景。二是治理能力顺应技术和健康的复合。新医科战略最为显著的提法就是新,但这种新绝非是对传统医学的颠覆性革新,而是在服务需求和提高质量的核心任务之下,对传统医学进行继承性创新。既需要有效解决患者的身体健康,也需要应对医科领域的技术健康,这产生了对医学领域的治理需求,催促着对医学领域相关制度、规范、主体以及环境予以廓清和重塑。三是技术适用需顺应业务和道德的复合。业务和道德一直是医学人才培养的二元旋律,当前新医科战略对于技术的需求激增,不仅仅是技术治疗疾病的需求增加,运用技术丰富医学教育的需求也在增加。智能相关技术在诸多方面呈现出与传统技术不同的表征,但对于相关技术的适用仍需要回归业务和道德的二元逻辑,技术课程的开展要匹配相应的伦理教学,医科人才对于技术的适用力要遵循业务和道德的基本准则,要用技术,更要用好技术。
4. 新医科战略下找准医学人才培养中法治教育定位的几点建议
法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基础性学科,是医学与人文学科融合的着力点。基于法治教育对于医科人才需求的双重弥合,一是回应新医科战略中的人才要素,二是回应新医科战略中的现实要素。法治教育对于新医科战略对卓越医科人才培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精准法治教育在医科人才培育中的定位,是进行医学、法学进行学科交叉融合培养的前提。
4.1. 通过法治教育规避医疗风险,审慎智能技术的单向嵌入
法治教育能够回应智能社会的技术变革,从而平衡效率和价值,促使医者合理审慎使用技术。通过法治教育,能够提升医科人才的规则思维、平等思维和底线思维,促使医学人才在医疗事务中,面对技术和价值的对冲,熨平能力褶皱,从而有效承接智能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嵌入。规制思维能够帮助医科人才时刻以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标准审视相关技术的适用,在效率和效能之间依据既有的医学理论和法治理论作出节制性判断,从而发挥医者的主体性作用,对工具性的技术进行有限度、有界限以及有选择的进行适用,避免医疗手段过度的技术主义和事本主义,补足价值主义和人本主义情怀。底线思维能够帮助医科人才提升对于风险感知的能力,并非仅仅是医学风险感知的能力,还包括由医学风险引发的并与其他领域风险互相勾连、互相作用的全域风险。以医者的视角对患者诊断全周期、全过程进行医学+其他学科的知识研判,从而控制医学风险作用的范围,规避医疗风险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演化成社会性风险。合理思维能够帮助医科人才提升运用技术手段的温度,尽管智能技术嵌入下的医疗器械或者医疗手段缺乏主体为人的温情和软度,但是通过对操作者、实施者的法治教育,能够以价值和观念浸润业务,将法治中的诸如“以人民为中心”等概念进行医学化诠释,从而打破医者和患者的技术隔层,传递医者的仁心仁术。综上,智能技术的单项嵌入规避技术过度适用的发散隐患,而对医科人才进行法治教育能够修正使用技术的意识和水平,从而对技术单向嵌入进行反向回应。
4.2. 通过法治教育疏解医患矛盾,营造新型和谐的医患关系
法治教育能够回应患者权利意识觉醒,匹配相应医者的法治素养和能力,规范调节医患关系。基于社会信息化和数据化,患者的权利意识觉醒乃至活跃,若医者无法匹配相应的素质和能力,就无法对患者的需求进行有效回应。这里的有效回应包括满足合理需求、限制不合理需求以及补足未主张的合理需求,这就要回归到医患关系上讨论。良好的医患关系,绝非医生主导下的专业性服从关系,也绝非患者需求主导下的回应性给予关系,而是要在法治的前提下形成规范性的协商关系。因此以法治教育培养医科人才的规范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规范思维主要有以下功能:一是规范思维能够形成医患合作的良性稳态,患者的权利主张、医者的专业指导都需要通过平等有效的规范结构来调和,但并非社会资源或者社会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而是以寻求最好的临床结局或疾病转归为目的的同向调节,双方的对话协商需要遵循法治的要求,严格依据相关规范依据约束行为;二是规范思维能够有效化解医患纠纷,医患纠纷是医患关系的消极形态,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就需要法治的手段、程序和机制来解决矛盾。规范化解路径能够提升医患双方的认可度,能够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行为方式[19]。
4.3. 通过法治教育重塑医学环境,以教育人文性反哺手段科技性
法治教育能够应对医科事务复杂化多样化需求,重塑新医科战略下的科技与人文并重的发展环境。医学属于自然科学,法学属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更多是对无意识的自然界的反映,社会科学是对能动性的人类世界的反映,因此通过社会科学的浸润能够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嵌入,实现对自然科学的价值引导,从而实现科技和人文的交流与融合。而法治教育正是依循这种学科间的作用完成对医科教育环境的重塑,新医科战略中的智能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同样是无意识的,但只有技术本身才能阻消技术带来的隐患,因此需要对行使技术的人进行教育指导和价值浸润,从而形成共有规则和普适理念,区别智能技术在医学领域可以适用的和不可以适用的事项,以有效预见智能技术带来的风险和隐患。新医科战略中的科技性无需多言,新医科的提出就是着眼于技术的嵌套和适配,但是需要在技术的硬度之外填补人文的软度,这就需要法治教育的填补。前端的技术路径已经依循相关的要求展开,而传统医学教育的范式还未来得及进行转变,即使存在一定转变也是简单进行技术演绎的拿来主义,需要立足更深层次的本质,以对医学人才的法治教育作为补正技术主义的持续动力,通过人才的塑造反哺新医科战略的技术实践,从而以法治教育的实质性作用为新医科战略的实施持续输出人文情怀的理论补给。
5. 结语及展望
新医科战略下注重对医科人才的法治教育,不仅仅是顺应医科领域全面深化依法治国的必然趋势,也是有效回应新医科战略人才需求的路径选择。一方面,通过法治教育提升医者合理、有效处理医患关系的能力,从而疏解医患关系带来的现实风险;另一方面,通过法治教育提升医者规范、审慎使用医疗技术的能力,从而应对新型医疗手段引发的潜在风险。此外,法治教育融入传统医学教育所带来“医学+法学”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契合新医科战略中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需明确的是,法治教育应以常态教育、深度教育和实践教育的模式与传统医学教育体系展开有机结合,以持续、有效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法学知识供给形式来融入医学人才培育的全过程,包括学位教育阶段(本科、硕士和博士)以及毕业后的教育(住院医师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等阶段,但需要在各阶段有所侧重,如在学位教育阶段侧重法学知识的理论输入、在住院医师培训时期侧重对医患关系规范处置的实践输入等等,方可将法治教育和医学教育有效融合,培育高质量的新医科人才。
* * *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Funding Statement
四川省社科“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十四五’期间四川省社会安全防控体系构建研究”(No. SC21ZD006)资助
Contributor Information
陈晨 周 (Chen-chen ZHOU), Email: chenchenzhou5510@scu.edu.cn.
业勋 胡 (Ye-xun HU), Email: 26925480@qq.com.
彦博 王 (Yan-bo WANG), Email: 418493773@qq.com.
References
- 1.钮晓音, 郭晓奎 “新医科”背景下的医学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21;(5):1–2. doi: 10.3969/j.issn.1002-1701.2021.05.001. [DOI] [Google Scholar]
- 2.顾丹丹, 钮晓音, 郭晓奎, 等 “新医科”内涵建设及实施路径的思考.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8;(8):17–18. doi: 10.3969/j.issn.1002-1701.2018.08.008. [DOI] [Google Scholar]
- 3.吴岩 新工科: 高等工程教育的未来——对高等教育未来的战略思考.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8;(6):1–3. [Google Scholar]
- 4.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 》. (2018-10-08)[2021-9-22].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740/s7952/201810/t20181017_351901.html.
- 5.王旭, 崔轶凡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体系对新医科人才培养的启示.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0;(4):261–264. doi: 10.3760/cma.j.cn115259-20190622-00497. [DOI] [Google Scholar]
- 6.李刚, 周学东 新医科战略中口腔医学教育发展的思考.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2021;52(1):70–75. doi: 10.12182/20210160302.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7.胡业勋, 王彦博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智能化嵌入困境及优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6(4):130–139. [Google Scholar]
- 8.张文显 构建智能社会的法律秩序. 东方法学. 2020;(5):4–19. doi: 10.3969/j.issn.1007-1466.2020.05.001. [DOI] [Google Scholar]
- 9.申卫星 医患关系的重塑与我国《医疗法》的制定. 法学. 2015;(12):79–91. [Google Scholar]
- 10.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2020-09-23)[2021-9-25].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9/23/content_5546373.htm.
- 11.卿平,曾锐,金泓宇, 等 重构教育体系, 推动面向未来的医学教学模式变革.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0;20(8):878–882. [Google Scholar]
- 12.刘吉臻, 翟亚军, 荀振芳 新工科和新工科建设的内涵解析——兼论行业特色型大学的新工科建设.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9;(3):21–28. [Google Scholar]
- 13.彭树涛 “新医科”的理念与行动.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28(5):145–152. [Google Scholar]
- 14.何珂, 汪玲 健康中国背景下“新医科”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工程科学. 2019;21(2):98–102. [Google Scholar]
- 15.唐娟, 郑葵阳, 谈在祥 多元主体视角下应用型新医科人才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对策. 职业技术教育. 2019;40(35):77–80. doi: 10.3969/j.issn.1008-3219.2019.35.020. [DOI] [Google Scholar]
- 16.沈瑞林, 王运来 “新医科”建设逻辑、问题与行动路径研究. 医学与哲学. 2020;41(12):69–73.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0.12.16. [DOI] [Google Scholar]
- 17.尹若兮 新医科背景下高等医科院校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研究.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2020;34(5):575–577. [Google Scholar]
- 18.尚丽丽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医学研究生学报. 2018;31(10):1078–1081. [Google Scholar]
- 19.张文显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法学. 2014;(4):5–27. [Google Sch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