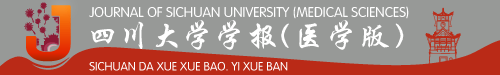Abstract
目的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数据了解全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群抑郁情况以及影响因素,为提高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缓解其抑郁症状提供实证依据。
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流行病学调查用抑郁量表(CES-D)评定抑郁患病情况,使用两水平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抑郁症状患病率的影响因素。
结果
采用本次调查中抑郁得分的第80个百分位数得分为临界值,结果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3.61%;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患抑郁症状;丧偶者患抑郁的风险更高;文化程度越高,患抑郁的可能性越低;农村地区中老年更容易患抑郁;患慢病和自评健康差的中老年人患抑郁风险更高;睡眠时间是患抑郁症状的一个保护因素。在控制了以上个体层面因素后,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中老年患抑郁的可能性低于内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结论
相关卫生部门应该重点关注女性、丧偶、慢性病中老年的抑郁症状问题;在农村地区和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国家应投入更多的卫生资源,预防和改善中老年的抑郁患病情况。
Keywords: 抑郁症状, 中老年人, 影响因素, 多水平统计模型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depress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 populations aged 45 and above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data from the 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and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and the alleviation of their depressive symptoms.
Methods
The source of the research data was the 2018 CFPS.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was used to assess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 two-level two-category unconditional logistics regression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Results
The 80th percentile interval score of depression score was used as the critical value,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as 23.61%. It was more likely for women to suffer from depressive symptoms than it was for men. Widowed individuals were at an even higher risk for having depression. The more education one had, the lower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depressio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in rural areas we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depressio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and self-rated poor health were at higher risk of depression. Sleep time is a protective factor that suppressed symptoms. After controlling the above-mentioned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in coastal and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were less likely to suffer from depression than those from inland and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did.
Conclusion
The health departments concerned should focus on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women, widowed individuals, and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In rural areas and underdeveloped inland regions, the state should invest more health resourc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improvement of depression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Keywords: Depressive symptoms,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fluencing factors, Multilevel statistical models
近年来,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越来越受到社会和政府的广泛关注,而是否抑郁则是心理健康重要的评价指标[1]。国内外关于抑郁的研究表明,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不仅对中老年人生活质量、日常生活能力、自杀率等有着重要影响,还会增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这些影响不仅严重降低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同时也给家庭乃至社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目前已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2-4]。众所周知,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阶段性发展的过程,因此关注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的抑郁情况,对于预防中老年人抑郁症的发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1980年至2000年间的研究表明,我国中老年人群抑郁症状患病率尚较低(4.14%~16.55%)[5-7]。但曹裴娅等[1]利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数据分析发现在全国水平上中老年抑郁症状患病率已高达31.9%;随后,刘梦琪[8]使用2015年CHARLS数据进行研究,发现34%的受访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鉴于目前抑郁症状患病率的上涨以及抑郁症状所给中老年人带来的危害,本研究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数据估计目前全国的中老年人抑郁症状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考虑到CFPS数据在抽样上采用的是多阶段复杂抽样[9],样本人群在不同的地域间可能存在集聚性,违背了数据独立性的假设,使得参数估计产生偏误[10],因此本研究采用多水平统计方法,分析中老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以使得结果更加的科学和准确,同时还能为我们提供影响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地域间的效应[11],为进一步改善和预防全国中老年人群的抑郁症状提供决策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调查对象
CFPS是一个综合性、全国性的社会追踪调查项目,其采用了内隐分层(implicit stratification)、多阶段、多层次、以及与人口规模呈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 PPS)[9],收集了居民个体、家庭、社区3个层次的数据。该方法保证了样本的全国代表性。而本次研究使用的是2018年CFPS最新数据,样本人群是来自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去除缺失值后,最终纳入10 838人。
1.2. 调查内容
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户口地区和工作情况)、抑郁症状情况(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量表)、客观健康状况(两周内是否不适、是否患慢病)、主观健康状况(自评健康)、健康相关行为(吸烟情况、饮酒情况、锻炼、睡眠时长等)。
1.3. 抑郁症状测量
CES-D量表是1977年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编制,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用于测量抑郁症状的量表之一,该量表经过诸多学者的研究和测量,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2]。原始的CES-D量表有20个条目,本次研究所使用的CES-D量表有8个条目,这8个条目分别为:①我感到情绪低落;②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③我的睡眠不好;④我感到愉快;⑤我感到孤独;⑥我生活快乐;⑦我感到悲伤难过;⑧我觉得生活无法继续。在受访中,被调查对象回答如下问题:“下面是一些您可能有过的感受或行为,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指出在过去一周内各种感受或行为的发生频率。共有4个选项:几乎没有(不到1 d)、有些时候(1~2 d),经常有(3~4 d)、大多数时候有(5~7 d)。”各条目四个等级依次计分为0、1、2、3分,其中4题和6题为反向计分,即3、2、1、0分。8个条目合计得分为24分。因为如今相关学者大多使用10条目或20条目的CES-D量表,而对于8条目的CES-D量表缺少统一临界值,因此本研究采用Radloff(1991)所建议的使用第80个百分位数得分[13]作为抑郁症状的临界值,相关研究也已证明该取值范围的合理性[14]。本次调查中抑郁得分的第80个百分位数得分为10分,因此当CES-D量表得分≥10分,则表明该中老年人患抑郁症状。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Stata15.1对数据库进行整理,首先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描述调查对象基本特征及是否患抑郁症状;然后再进行多因素影响分析,在这个过程中,考虑到全国不同省份/直辖市的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群抑郁症状可能存在地区间的聚集性,不满足样本观测独立性的假设,从而导致参数估计的偏误,因此先拟合两水平零模型,对高水平的残差方差在α=0.05的检验水准上进行统计学检验,若P<0.05,则表示抑郁症状在高水平存在聚集性,违背了数据独立性的假设,故应使用多水平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抑郁症状的多因素分析,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估计值。最后,在参数的估计方法上,本研究选择极大似然函数估计方法,该方法在结局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时,也是最为常用的参数估计方法。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共纳入10 838位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男女比例相当;平均年龄(59.19±9.74)岁;在婚9 627人,占比88.83%,其次为丧偶924人,占比8.53%;文化程度以文盲/半文盲居多,占比34.19%,其次为小学2813人,占比25.95%,大专及以上最少,占比3.76%;农业户口为8 009人,占比73.89%;在业人数为7 398人,非在业为3 440人;患有慢性病人数占比22.62%;过去一周锻炼频次均数为(3.01±3.60)次;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人占比23.94%,自评健康状况好的人占比59.95%。
2.2. 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分析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调查人群的抑郁症状平均得分为(7.69±3.09)分,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3.61%。以调查对象居住地为高水平(水平2),居民个体为低水平(水平1),利用两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对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首先对数据是否具有聚集性进行假设检验,拟合不含任何解释变量的零模型,结果显示,水平2(地区)残差方差为0.11(P<0.05),这说明调查对象抑郁症状在其所在地区间存在聚集性(表1)。
表 1. Null model on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in CFPS participants.
研究对象抑郁症状两水平零模型
| Parameter | Estimates | Standard error | P |
| Fixed effects (constant) | −1.232 | 0.073 | <0.001 |
| Random effect | - | - | - |
| 2nd level (province) | 0.112 | 0.038 | <0.05 |
| 1st level (individual) | 1 | - | - |
然后以是否有抑郁症状为因变量,采用两水平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将调查对象年龄、一周锻炼次数、睡眠时间以连续性形式中心化后纳入模型;分类变量以哑变量的形式纳入模型。结果显示,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的睡眠时间越长,其患抑郁症的概率就越低(OR=0.890, P<0.01);男性患抑郁症的风险低于女性(OR=0.667, P<0.01);已婚者与丧偶者相比,其患抑郁症的风险更低(OR=0.082, P<0.01);在文化程度方面,文化程度越高,其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就越低;在户口类型方面,农村户口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更高(OR=1.151, P<0.01);在健康因素方面,患慢病的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是非慢病人群的1.377倍(OR=1.377, P<0.01),自评健康为较好、一般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都低于自评健康差的人群(OR=0.408, P<0.01,OR=0.443, P<0.01)(表2)。
表 2. Results for the two-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in CFPS participants.
研究对象抑郁症状两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
| Variable | β | SE | OR (95%CI) |
| β: 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 CI: Confidence interval; OR: Odds ratio; SE: Standard error. ** P<0.01, *P<0.05. | |||
| Constant | 0.75 | 0.20 | 0.87 (0.50, 1.51) |
| Age | 0.01 | 0.01 | 1.00 (0.99, 1.01) |
| Frequency of exercise | −0.01 | 0.01 | 0.99 (0.98, 1.01) |
| Sleeping time/h | −0.12** | 0.01 | 0.89 (0.87, 0.92) |
| Gender (women) | |||
| Men | −0.41** | 0.07 | 0.67 (0.59, 0.76) |
| Marital status (widowed) | |||
| Unmarried | 0.31 | 0.21 | 1.37 (0.90, 2.06) |
| Married | −0.53** | 0.08 | 0.59 (0.50, 0.69) |
| Divorced | 0.09 | 0.20 | 1.21 (0.74, 1.63) |
| Education level | |||
| Illiterate | 0.83** | 0.18 | 2.30 (1.63, 3.25) |
| Primary school | 0.55** | 0.18 | 1.74 (1.23, 2.45) |
| Secondary school | 0.48** | 0.17 | 1.61 (1.15, 2.27) |
| High school | 0.19 | 0.18 | 1.21 (0.85, 1.73) |
| Employment status (unemployed) | |||
| Working | 0.01 | 0.06 | 1.01 (0.90, 1.14) |
| Typ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 | |||
| Rural | 0.14* | 0.07 | 1.15 (1.00, 1.32) |
| Chronic disease status (no) | |||
| Yes | 0.32** | 0.06 | 1.38 (1.23, 1.54) |
| Self-reported health status (poor) | |||
| Good | −0.90** | 0.06 | 0.41 (0.37, 0.46) |
| General | −0.82** | 0.08 | 0.44 (0.38, 0.51) |
| Smoking status (no) | |||
| Yes | 0.05 | 0.07 | 1.05 (0.92, 1.20) |
| Drinking status (no) | |||
| Yes | −0.07 | 0.07 | 0.94 (0.81, 1.08) |
为了进一步了解在控制了个体层面影响因素后,地域因素是否为45岁及以上中老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我们进行了残差分析。结果(图1)显示,浙江、福建、江苏等沿海城市的45岁及以上中老年抑郁症状检出率低于甘肃、重庆、山西、贵州、陕西等内陆城市。
图 1.

Residual analysi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aged 45 and older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municipality/autonomous region
不同省/直辖市/自治区45岁及以上中老年抑郁症状残差分析
3. 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2018年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3.61%,低于曹裴娅等[1]利用2013年CHARLS数据得出的31.9%,李甲森等[4]利用2013年CHARLS数据得出的31.2%,以及刘梦琪利用2015年CHARLS数据得出的34%[8]。这可能是由于选择了不同形式的CES-D量表来测量抑郁症状所引起的。因此本研究为验证该结论,同时为提高本次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同时参考ZHOU等[14]的研究结果重新将抑郁得分的第75个百分位数作为抑郁症状的临界值,此时临界值为9分,抑郁症状检出率为33.60%,重新将新的抑郁分组作为因变量,利用两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纳入与之前相同的自变量,结果显示(因篇幅限制未列出)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群患抑郁的影响因素仍然和以10分作为抑郁临界值的影响因素一致,这表明了本次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此次研究发现,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女性相比男性,其患抑郁的可能性更高,由于女性本身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特质[15],使得女性往往对接触到心理应激事件表现得更加敏感,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16-17];文化程度越高,其患抑郁的可能性就越低,这与我国学者对于中老年人抑郁研究的结果一致[4]。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越高,其更有能力解决相关问题和调控负面情绪;丧偶的中老年人,其患抑郁可能性更高,因为丧偶本身作为心理应激事件,对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就是一种打击,因此其更可能患抑郁症状;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相比城镇中老年人其患抑郁的可能性越高,这是因为农村中老年人无论是在经济条件还是社会地位,都与城市中老年人有较大的差距,具体可表现在社会保障、就业条件、生活便利程度及就医环境等,这和国内研究结果一致[18];而中老年人的睡眠时间是抑郁的一个保护因素,其睡眠时间越长,患抑郁的可能性也就越低。这和很多研究结果一致[19],睡眠时间越长,其失眠的可能性就越低,而失眠与抑郁息息相关,长期失眠将导致严重抑郁症状的发生[20]。
在健康方面,患慢病的中老年人其更可能患抑郁,慢性病因为其病程迁延不愈,对患者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更可能患抑郁。自评健康作为广泛使用的综合的主观健康评价指标,而抑郁症状本就是心理健康的一个评价指标,因此自评健康良好,其抑郁的可能性就越低[21-22]。
在控制了以上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后,本研究发现在我国沿海及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浙江、福建等地的中老年人患抑郁的概率要低于我国内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如甘肃、山西、贵州等地。尽管重庆市作为我国的四大直辖市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数据显示,重庆市GDP为2.04万亿元,甚至高于与沿海某些城市如杭州(1.35万亿)、泉州(0.85万亿),但重庆市中老年人较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的中老年人更易患抑郁。因此针对此现象,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讨论,虽然谢颖等[23]对重庆市老年人的抑郁及焦虑进行了研究,检出率分别为57.2%和40.8%,从数据上来看确实远高于本次研究抑郁检出率,但是由于其研究对象为老年人,所以并不足以解释本次研究所发现的重庆地区对于中老年抑郁症状效应。这同时也是本次研究的不足之处,由于缺乏水平2(地区)上的相关变量,使得我们对于地区效应的解释力度不够,但残差分析却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此外本次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不能说明患抑郁与其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效应,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解释抑郁和相关因素的因果效应。
综上,针对女性、丧偶、患慢病的中老年人,相关卫生部门应重点关注其抑郁症状问题,同时也应加强对于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健康教育及医疗干预;对于农村以及内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的中老年人,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制定合理的社会保障措施,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完善生活相关的便利措施。
* * *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提供的CFPS数据。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Contributor Information
念韦 吴 (Nian-wei WU), Email: 2511760748@qq.com.
宁秀 李 (Ning-xiu LI), Email: liningxiu@163.com.
References
- 1.曹裴娅, 罗会强, 侯利莎, 等 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抑郁症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6;47(5):763–767. [PubMed] [Google Scholar]
- 2.辛琦, 王宇, 兰棱 家庭人口结构对中国老人抑郁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现代营销(信息版) 2019;(5):218–221. [Google Scholar]
- 3.JOHN A, PATEL U, RUSTED J, et al Affective problems and decline in cognitive state in older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sychol Med. 2019;49(3):353–365. doi: 10.1017/S0033291718001137.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4.李甲森, 马文军 中国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公共卫生. 2017;33(2):177–181. doi: 10.11847/zgggws2017-33-02-02. [DOI] [Google Scholar]
- 5.吴文源, 张明园 忧郁量表CES-D大社区老人中的应用. 上海精神医学. 1989;7(3):139–142. [Google Scholar]
- 6.孟琛, 汤哲 北京城乡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分析与比较.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0;20(4):196–199. [Google Scholar]
- 7.崔才三, 丁守銮, 胡平 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及影响因素分析. 山东医药. 2000;40(20):1–3. doi: 10.3969/j.issn.1002-266X.2000.20.001. [DOI] [Google Scholar]
- 8.刘梦琪. 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及政策建议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 2018.
- 9.谢宇, 张晓波, 涂平, 等.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用户手册. 第3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10.杨珉, 李晓松. 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常用多水平统计模型.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 1-4, 69-75.
- 11.NING M, ZHANG Q, YANG M Comparison of self-reported and biomedical data on hypertension and diabetes: Findings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BMJ Open. 2016;6(1):e009836[2021-04-13]. http://dx.doi.org/10.1136/bmjopen-2015-009836. doi: 10.1136/bmjopen-2015-009836.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2.RADLOFF L S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ppl Psychol Meas. 1977;1(3):385–401. doi: 10.1177/014662167700100306. [DOI] [Google Scholar]
- 13.RADLOFF L S The use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J Youth Adolesc. 1991;20(2):149–166. doi: 10.1007/BF01537606.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4.ZHOU Q, FAN L, YIN Z Association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Psychiatry Res. 2018;259:81–88. doi: 10.1016/j.psychres.2017.09.072.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5.苏宝兰, 孙福刚, 云维生, 等 抑郁症的性别差异.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2008;18(2):97–98. doi: 10.3969/j.issn.1005-3220.2008.02.008. [DOI] [Google Scholar]
- 16.郭薇, 周圣凡, 韩金松, 等 沈阳市65岁及以上社区老年人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14;18(11):1024–1027. [Google Scholar]
- 17.LIM G Y, TAM W W, LU Y, et al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in the community from 30 countries between 1994 and 2014. Sci Rep. 2018;8(1):2861[2021-03-12].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18-21243-x. doi: 10.1038/s41598-018-21243-x.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8.陶娜, 尹平 我国中老年人群抑郁发生率的城乡差异及危险因素研究.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17;34(1):22–25. doi: 10.3969/j.issn.1673-5625.2017.01.008. [DOI] [Google Scholar]
- 19.王宏, 王丹, 杨媛, 等 老年人群抑郁症状与睡眠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实用老年医学. 2019;33(2):177–181. doi: 10.3969/j.issn.1003-9198.2019.02.018. [DOI] [Google Scholar]
- 20.LOPRESTI A L, HOOD S D, DRUMMMOND P D A review of lifestyl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important pathways associated with major depression: Diet, sleep and exercise. J Affect Disord. 2013;148(1):12–27. doi: 10.1016/j.jad.2013.01.014.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21.马静怡. 老年抑郁、焦虑与认知功能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关系研究.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 2014.
- 22.何民富. 抑郁在中国中老年慢性病人群中的流行情况及其对慢性病患者的影响研究. 长春: 吉林大学, 2019.
- 23.谢颖, 陈小异 重庆市老年人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7;37(12):3060–3062. doi: 10.3969/j.issn.1005-9202.2017.12.092. [DOI] [Google Sch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