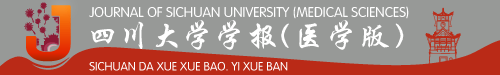Abstract
严重烧伤感染早期,机体天然免疫细胞杀伤功能持续低下,引起免疫系统持续代偿性分泌大量细胞因子,以提高抗细菌感染能力;细胞因子分泌一旦失控,就会形成细胞因子风暴。严重烧伤感染后期,持续的急性髓系增生引起的骨髓动员能力耗竭、免疫应答水平低下、促修复的抑炎因子分泌增加,将导致机体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烧伤感染后,细胞因子风暴是由过度的促炎刺激、炎症调节不足或两者共同引起。本文拟从免疫学角度,就严重烧伤感染后机体抗病原菌感染免疫反应的改变进程,严重烧伤感染早期细胞因子风暴和后期机体免疫抑制状态的发生及转化机制做一简要总结。未来研究方向建议从以下方面展开:严重烧伤后先天免疫细胞细菌杀伤功能低下的机制,急性髓系增生导致髓系抑制细胞(MDSC)和有核红细胞增多在细胞因子风暴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巨噬细胞吞噬杀伤细菌功能障碍与分泌细胞因子功能亢进的关键调节机制,巨噬细胞M1型/M2型以及效应T细胞/调节性T细胞动态平衡破坏在引发机体免疫抑制状态中作用及关键调节机制。
Keywords: 烧伤感染, 细胞因子风暴, 免疫抑制
Abstract
In the early stage of infection in severe burn patients, the killing function of the natural immune cells is continuously low, which causes the immune system to continuously and compensatorily secrete a large amount of cytokine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resist bacterial infection. Once the cytokine secretion is out of control, a cytokine storm will form. In the late stage of severe burn infection, the bone marrow mobilization caused by continuous acute myelodysplasia will be exhausted, the level of immune response will be low, and the secretion of anti-inflammatory factors promoting repair will be increased, which will lead to immune suppression. Cytokine storm after burn infection is caused by excessive proinflammatory stimulation, inadequate inflammatory regulation, or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munology, this review will briefly summarize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immune response against pathogenic bacteria after severe burn infection, cytokine storm in the early stage of severe burn infec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occurr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immunosuppression in the late stage of severe burn infection. We suggest that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Mechanism of low bacterial killing function of innate immune cells after severe burn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acute myeloid hyperplasia leads to myeloid inhibitory cells (MDSC) and nucleated erythrocytosi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ytokine storms; The key regulatory mechanism between macrophage phagocytic dysfunction and cytokine hyperactivity; The role and key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destruction of the dynamic balance of M1/M2 macrophages and effector/regulatory T cells in triggering immune suppression.
Keywords: Burn infection, Cytokine storm, Immunosuppression
严重烧伤后,由于机体皮肤等屏障的破损,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烧伤创面出现大量坏死组织和渗出液,为病原菌提供了合适的微环境[1]。烧伤面积越大、程度越深,受损的皮肤保护屏障就越多,病原菌感染就更严重[2],而且烧伤引起的高代谢状态更是增加了感染的概率和严重程度[3]。因此各种微生物极易通过破损的皮肤、受损的肠黏膜等侵入机体引发不同程度的全身性感染,其导致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是严重烧伤重要的并发症。近20余年来,广泛的基础和临床研究逐步揭示烧伤脓毒症是由病原微生物(主要是胞外细菌)与宿主免疫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引起的,发病初始阶段与免疫反应亢进引发促炎性细胞因子的级联放大反应失控有关,由此引入了“细胞因子风暴”的概念[4]。新近研究表明[5],随着疾病的发展,机体由免疫亢进向免疫抑制状态的转变导致全身性感染失控是严重烧伤感染引发MODS的重要原因。本文仅从免疫学角度,就严重烧伤感染早期“细胞因子风暴”和后期机体免疫抑制状态的发生、转化机制等做一简要思考总结,以期为读者提供一点思路和参考。
1. 严重烧伤感染后机体抗病原菌感染免疫反应的改变进程
严重烧伤后组织损伤和病原微生物感染导致内源性损伤相关模式分子(DAMPs)(如高迁移率族蛋白1(HMGB1)、线粒体DNA263、以及双链RNA)和外源性病原体相关模式分子(PAMPs)(如脂多糖和肽聚糖)的大量释放,直接刺激机体迅速启动包括固有的先天免疫反应和获得性免疫反应在内的免疫防御机制[6],免疫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等)在数小时内被激活,识别内源性因素(DAMPs或警报素),通过模式识别受体(PRR)即Toll样受体(TLRs)和NOD样受体(NLRs)与PAMPs结合,诱导先天免疫细胞分泌Ⅰ型干扰素、炎症因子和趋化因子,从而发挥抗感染免疫功能[7]。TLRs和NLRs通过其特异性配体的连接激活下游炎症途径,导致参与多种炎症介质〔如白细胞介素(IL)-1、IL-6、IL-8、IL-18和肿瘤坏死因子(TNF)〕释放的核转录因子(NF)-κB的激活,这些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释放促进炎症反应,可诱导血管渗漏、炎症反应和代谢变化。血管渗漏和血管内液体向外部空间的转移导致组织水肿和进一步损伤;炎症反应可导致免疫抑制和对细菌入侵的无效反应;代谢变化包括蛋白质降解加快、发热、呼吸急促和心脏负荷增加,最终发展为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8]。而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以及补体系统是机体先天免疫系统中直接清除感染细菌的主要效应细胞和分子;T细胞和B细胞则是获得性免疫的主要效应细胞,负责分泌大量细胞因子和针对病原菌特异性抗体,辅助吞噬细胞和补体系统更为高效地清除病原菌、控制机体感染。T细胞可杀伤靶细胞、参与特异性免疫应答和产生细胞因子等,B细胞除产生病原菌特异性抗体辅助吞噬细胞外,还可通过IL-10和IL-35来调节炎症免疫反应[9],IL-10是一种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细胞因子,可抑制多种免疫细胞的功能,间接或直接抑制机体炎症反应[10]。
1.1. 严重烧伤感染后负责直接杀伤病原菌的天然免疫功能持续下降机制
中性粒细胞作为清除病原菌最重要的效应细胞,在感染4~6 h内大量浸润到感染部位,是机体抗感染免疫的第一道防线。烧伤早期,中性粒细胞几乎占整个创面细胞的50%以上。当病原菌入侵时,中性粒细胞在趋化因子的诱导下迅速迁移至感染部位[11],发挥吞噬作用,防止病原菌的扩散以及全身炎症的发生[12]。中性粒细胞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模式识别、吞噬并杀伤病原体,还能通过释放活性氧、蛋白酶和抗菌蛋白以及部署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器(NETs)等非特异性杀伤病原体。另外,它们还可释放TNF-α,IL-1β,IL-6,趋化因子CCL2、CCL3CCL5和CXCL8,单核细胞趋化蛋白(MCP)-1等炎症因子招募巨噬细胞、T细胞及其他中性粒细胞至创面,进一步强化创面感染控制。TNF-α和IL-6与MODS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3];MCP-1的表达可以稳定炎症因子和趋化因子,并抑制因子导致的细胞损伤和凋亡[14]。TNF是先天免疫系统的主要介质,对于诱导针对感染、创伤或缺血的局部保护性免疫反应至关重要,然而过量TNF的产生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它在血液中扩散会导致心血管衰竭,在脓毒症休克的患者和实验模型中发现TNF会导致休克、低血压、血管内凝血,感染性休克中观察到特征性出血性坏死和组织损伤[15],中性粒细胞的这些功能在通过自我强化有效清除坏死组织和控制感染的同时,也加重了对周围正常组织的非特异性损伤[12]。严重烧伤后,外周血的中性粒细胞大量进入损伤组织导致机体中性粒细胞耗竭,而血管通透性增加引起的中性粒细胞丢失进一步加重了该情况。有研究指出,严重烧伤1~2周后,烧伤创面会出现白细胞浸润,烧伤越严重,浸润的白细胞就越少,进而影响杀伤病菌的能力[16]。中性粒细胞耗竭进而代偿性刺激骨髓粒细胞从骨髓原位迁移至损伤部位,并加强造血干细胞分化和髓系固有免疫效应细胞增殖(急性髓系增生)。急性髓系增生过程引起未发育成熟的具有免疫抑制效应和炎性[17]髓系抑制细胞(MDSC)扩增并大量进入外周循环。MDSC不能发育为成熟的中性粒细胞或巨噬细胞,但可以大量产生一氧化氮、活性氧、TNF-α等多种炎症介质,而且,MDSC可表达高水平的精氨酸酶(ARG)1,使得T细胞活化过程中所必须的精氨酸被降解,导致CD4+和CD8+ T细胞活化受阻,从而导致机体清除病原菌能力进一步下降和炎症介质进一步积累[18]。此外,MDSC可通过上调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因子(STAT)3的活性以及下调T细胞受体(TCR)相关ζ链而导致不能传递CD4+和CD8+ T细胞活化信号等[17],抑制T细胞的功能。有资料显示,抑炎因子IL-10可以促进MDSC的发育[19]。成熟中性粒细胞不能增殖且只有2~3 d生存周期,而MDSC能够在体内慢性扩增,进一步降低了机体抗感染能力。持续的中性粒细胞耗竭状态将导致骨髓动员能力下降、MDSC产生增多,直至骨髓动员能力枯竭、外周中性粒细胞数量显著下降、清除细菌能力出现障碍。当烧伤后合并严重感染时,常常出现由于骨髓动员能力枯竭而导致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明显减少、MDSC明显增多、功能障碍的情况,从而导致机体感染失控。
巨噬细胞既有吞噬杀菌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也通过加工提呈抗原在特异性免疫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巨噬细胞能合成和分泌近百种免疫化学分子,在烧伤后的感染控制和免疫功能紊乱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烧伤后2~4 d,巨噬细胞取代中性粒细胞,成为感染部位最主要的免疫效应细胞。巨噬细胞通过PAMPs受体(如清道夫受体、TLRs等)直接或通过补体或抗体介导方式(补体受体、Fc受体)间接识别、吞噬、杀伤病原菌。其中直接识别方式主要在感染早期抗体形成前发挥作用,但病原菌清除效率较低下,当抗体形成后能显著提高巨噬细胞的病原菌杀伤效率。巨噬细胞抗原递呈功能在增强效应T细胞功能中起重要作用,同时巨噬细胞对细菌的杀伤能力也需要T细胞分泌的相关细胞因子的辅助。巨噬细胞同时还可清理已凋亡的中性粒细胞,减轻正常组织的非特异性损伤。巨噬细胞能根据外界微环境的变化而极化为M1型和M2型[20]。M1型巨噬细胞是机体消灭病原微生物的主要效应细胞,可由干扰素(IFN)-γ和TNF-α等激活,释放IL-1β、IL-6、IL-12、IL-15、IL-23、TNF-α、巨噬细胞炎性蛋白(MIP-1)等促炎性细胞因子放大炎症反应[21-22],以及分泌炎性细胞趋化因子如MCP-1、CXCL10、CCL2、CCL5、CXCL8(IL-8)和CXCL9募集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NK)和辅助性T细胞(Th)至感染部位并促进Th1和Th17细胞的分化,能促进炎症反应,还能杀伤侵入的病原菌[23],烧伤病原菌感染初期,巨噬细胞向M1极化,其表面的模式识别受体(PRRs)识别PAMPs并释放大量炎性介质,以杀伤病原微生物[24]。但是持续的M1活化及其反应产物的生成也可导致细胞或组织损伤[25]。M2型巨噬细胞由IL-4、IL-10等抗炎细胞因子和糖皮质激素等激活,可释放多种抗炎因子缓解炎症反应以及促进组织修复[26]。其中,ARG1通过消耗精氨酸来抑制CD4+T细胞的应答;白介素受体拮抗剂(IL-1ra)可阻碍IL-1的促炎作用;转化生长因子(TGF)-β则通过诱导调节性T细胞(Treg)的分化(竞争抗原递呈细胞上的共刺激分子等)来发挥免疫抑制的作用;IL-10不仅可以直接抑制抗原呈递细胞,还能通过抑制IL-12、IL-23的合成影响Th1和Th17细胞的分化[27]。另外,Ym1(又称CHI3L3,几丁质酶3样蛋白3)、抵抗素样分子-α(Fizz1)等也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但它们的具体作用机制有待阐明。在严重烧伤合并感染时,巨噬细胞的数量、迁移能力、吞噬功能、杀伤效能、抗原递呈功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或抑制,致使病原菌清除能力和T细胞调节功能下降,而T细胞功能下降进一步降低巨噬细胞的细菌杀伤能力和B细胞的抗体产生,进而导致巨噬细胞细菌清除能力障碍;与此同时,巨噬细胞细菌清除能力障碍导致病原微生物大量持续增殖,引起巨噬细胞持续性代偿分泌大量炎性因子,并大量分化为M1型。当这些炎症因子不能有效促进机体免疫系统清除病原微生物时,就会导致炎症因子分泌失控[28],从而引发细胞因子风暴[29-30],使自身免疫系统和正常细胞组织受损[31]。
补体系统是机体直接清除病原菌微生物的另一条重要途径。补体激活途径包括经典途径、旁路途径以及凝集素反应/MBL途径。其中旁路途径和凝集素反应/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MBL)途径由细菌的细胞壁成分——脂多糖,以及多糖、肽聚糖、磷壁酸、PAMPs等直接启动形成膜攻击复合物溶解杀伤病原微生物[32],是感染早期未形成特异性抗体之前机体补体系统杀伤病原菌的主要方式,但效率不高。而补体经典激活途径需要抗原抗体复合物作为激活物,大大提高了补体对微生物的杀伤效率,是机体感染后期形成特异性抗体杀伤病原菌的主要方式。特征性补体系统的激活以及持续过度的免疫系统活化等因素会影响巨噬细胞与中性粒细胞对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等炎性介质的反应[33],从而分泌更多的氧自由基等刺激炎症介质,进一步加剧了炎症反应[34]。补体的裂解片段C2a、C3a、C4a和C5a等发挥强烈的趋化、免疫、激肽、过敏毒素样等作用,强烈吸引吞噬细胞向炎症部位聚集并调理其吞噬功能,还能够造成炎症局部毛细血管扩张和正常组织细胞的损伤。在严重烧伤合并感染时,由于各种原因致使补体系统清除微生物功能低下,感染部位病原微生物大量增殖持续刺激引起补体系统持续过度激活,从而导致补体裂解片段过度累积,加重感染失控风险及周围正常组织损伤。C3a和C5a可介导炎性活动,诱导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趋化、募集和活化;具有显著的过敏活性,导致肥大细胞脱粒和随后的释放血管活性胺(组胺和血清素)、白三烯、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TNF-α、IL-4等);还能直接激活内皮,介导通透性增加和黏附分子表达,刺激血小板活化[35]。
1.2. 严重烧伤感染后获得性免疫反应由代偿性升高向低下转变的机制
获得性免疫由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共同组成,分别在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中发挥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类细胞并不直接参与对外来病原菌的杀伤,而是通过调节吞噬细胞和补体系统的细菌杀伤功能来完成它们的抗病原菌感染职能。处于静息状态的初始CD4+T淋巴细胞在递呈病原菌抗原的树突状细胞的辅助下被激活,分化为Th17、Th1、Th2等细胞亚型并发挥其特殊的抗感染免疫功能。其中,Th17细胞分泌IL-17、IL-22等促炎症因子,是对抗细胞外细菌及霉菌的免疫反应的重要效应细胞,主要通过强烈的招募中性粒细胞执行病原菌杀伤功能[36],在介导自身免疫性和感染性疾病的发病机理中起作用[37];Th1细胞分泌IL-2、IFN-γ、TNF等细胞因子,是对抗细胞内细菌及原虫的免疫反应的重要效应细胞,并具有促进巨噬细胞的完全活化并增强吞噬细胞的细菌杀伤能力;Th2细胞分泌IL-4、IL-5、IL-10和IL-13等细胞因子,主要辅助B细胞活化并促进B细胞增殖、分化和抗体的生成。在烧伤状态下,B细胞受体信号通路受到抑制,其增殖分化能力也被抑制[38]。Th1和Th2的功能是互相拮抗的,机体免疫调节的一个重要机制就在于Th1与Th2细胞间的相互影响和功能间的相互平衡[39]。抗体可与相应的抗原特异性结合,激活补体大幅度提升补体系统对病原菌的清除效率,促进吞噬细胞特异性吞噬杀伤病原菌能力,并能中和毒素,对多种病原微生物具有抑制效应。由于烧伤感染大多数情况是胞外菌引起的,因此,获得性免疫主要围绕提高天然免疫对细菌的清除效应发挥功能。严重烧伤感染引发的天然免疫功能障碍会使得获得性免疫反应代偿性升高,并大量分泌各类炎症因子,当这些因子持续累积直至失控时,则会引发炎症因子风暴[40]。而当严重烧伤合并多次感染时,骨髓动员能力枯竭引起外周天然免疫细胞与T/B淋巴细胞数量和功能都会出现显著下降,导致机体免疫反应被全面抑制,感染失控。
2. 严重烧伤感染早期细胞因子风暴形成及后期免疫抑制状态的转化机制
有资料显示,人和小鼠等在严重烧伤后,获得性免疫处于抑制状态[41],严重烧伤感染后,机体启动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补体系统通过吞噬和分泌大量生物活性介质直接杀伤入侵微生物。由于皮肤免疫和物理屏障的大面积损毁和外周中性粒细胞储备耗竭导致机体抗感染能力的显著下降,在不断积累的内源性DAMPs和外源性PAMPs持续刺激下,①以M1型巨噬细胞、Th1/Th2/Th17淋巴细胞为代表的促炎免疫细胞大量分泌炎性因子形成复杂的“损伤性”细胞因子网络,一方面通过协同作用刺激骨髓急性髓系增生产生并释放更多的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T细胞及巨噬细胞:多能集落刺激因子(Multi-CSF)、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等〕、加强外周免疫细胞招募(Th17:IL-17A和各类趋化因子等)、增强巨噬细胞活化及杀菌功能(Th1:IFN-γ、TNF等)、活化B细胞分泌抗体提高吞噬细胞及补体细菌清除效率(Th2:IL-4、IL-13等),从而提高机体的天然免疫清除病原菌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诱导炎症周围组织毛细血管形成血栓切断病原微生物的血液传播途径(TNF-α)来局限感染范围,但同时也进一步加重了周围正常组织的非特异性损伤。②以M2型巨噬细胞、Th2/Treg淋巴细胞为代表的抑炎免疫细胞大量分泌抑炎因子形成复杂的“修复性”细胞因子网络,一方面通过分泌抑炎因子抑制M1型巨噬细胞分化及功能(ARG1、IL-4、IL-10等)、Th1/Th17淋巴细胞分化及功能〔Th2/Treg:IL-4、IL-13、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等〕来下调炎症因子产生,保护周围正常组织,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天然免疫的活化和细菌杀伤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分泌大量生长因子促进损伤组织修复〔TGF-β、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血小板衍生因子(PDGF)等〕,同时通过纤维化来限制病原菌向周围正常组织扩散。这与目前学界关于SIRS和代偿性抗炎症反应综合征(CARS)同时发生的观点一致。由于严重烧伤早期引起天然免疫细胞杀伤功能低下引起“损伤性”细胞因子网络分泌失控,从而导致全身性的细胞因子风暴。细胞因子风暴发生时,多种细胞因子如TNF-α、IL-6、IL-12、IFN-γ和MCP-1等大量产生,趋化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等至感染部位,高效性杀伤病菌微生物的同时也严重损伤自身器官组织[42],损伤最重的靶细胞是血管内皮细胞,致使微血管床形成大量血栓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大量血栓形成后会激活纤维溶解系统,导致纤溶亢进;另外因严重烧伤感染早期凝血蛋白被大量消耗,后期凝血物质不足导致低凝期,机体出现多发微血管出血并出现继发性纤溶亢进,最终形成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加重器官缺血[43]。然而,临床上严重烧伤患者早期出现的MODS很少是全身性的细胞因子风暴所导致,一方面因为现代抗生素和ICU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是因为严重烧伤患者由于休克、高代谢等负面状态等而致使免疫反应处于低水平状态。
严重烧伤合并反复感染引起机体由免疫过强向免疫抑制状态的可能转化机制如下:①机体通过不断代偿性骨髓急性增生缓解外周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储备耗竭,引起免疫抑制性MDSC不断释放至外周血并在体内扩增;②持续代偿性骨髓急性增生导致骨髓动员能力枯竭,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以及T/B淋巴细胞等全谱系免疫细胞产生减少;③机体抗病原菌感染免疫功能的持续下降,导致内源性DAMPs和外源性PAMPs过度积累和持续刺激机体免疫系统,致使免疫细胞处于无应答状态,进而加剧机体病原菌清除免疫功能障碍;④病原菌清除免疫功能障碍和组织损伤进一步诱导机体代偿性增强“修复机制”,通过纤维化方式限制细菌扩散,导致机体免疫抑制状态的恶化。机体持续处于免疫抑制状态且不断恶化的结果就是反复感染,感染失控,引起内源性DAMPs和外源性PAMPs大量入血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可诱发全身性免疫功能障碍[44],并最终导致DIC和MODS。
3. 小结与展望
由于细胞因子风暴和免疫抑制状态导致的感染失控是严重烧伤感染后出现MODS的重要原因,探索其发生发展机制,形成有效的治疗方法显得尤为迫切。严重烧伤感染早期,机体天然免疫细菌杀伤功能持续低下引起机体免疫系统持续代偿性分泌大量细胞因子提高抗细菌感染能力,导致细胞因子分泌一旦失控就会形成细胞因子风暴。后期由于持续的急性髓系增生引起的骨髓动员能力耗竭、免疫应答水平低下、促修复的抑炎因子分泌增加将导致机体处于免疫抑制状态。而严重烧伤感染早期引发细胞因子风暴和后期机体免疫系统功能障碍所导致的大量细菌/组织毒素入血都是通过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形成DIC,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MODF)。
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笔者建议要着重解决下列关键问题:① 由于先天免疫细胞细菌清除功能低下是导致细胞因子风暴的关键始动因素,导致严重烧伤后中性粒细胞及单核巨噬细胞细菌杀伤功能低下的关键分子机制是什么?② 持续急性髓系增生在大量动员中性粒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产出的同时,还产生大量的MDSC和有核红细胞,这些细胞在烧伤后细胞因子风暴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机制是什么?③ 单核巨噬细胞细菌杀伤功能低下和细胞因子分泌亢进在细胞因子风暴发生发展过程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导致这种现象的关键分子调控机制是什么?④ 巨噬细胞M1型与M2型以及效应T细胞与调节性T细胞是构成机体免疫动态平衡网络的关键环节,该网络平衡的破坏是导致细胞因子风暴形成以及机体免疫抑制状态的关键原因之一,该网络平衡的维持及破坏的关键调节机制是什么?
本文仅对烧伤炎症失调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转向免疫抑制状态机制做了简单的阐述,希望未来通过深化对细胞因子风暴、免疫抑制状态以及烧伤脓毒症的发生发展本质的认识,能够有效地减小细胞因子风暴危害和减少全身性感染失控以及多器官损害等烧伤并发症的发生,并为烧伤感染的免疫疗法开辟新途径。
Funding Statement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No. 816300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No. 31872742)、军队医学科技青年培育计划拔尖项目(No. 20QNPY024)和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科学基金(No. cstc2019jcyj-cxttX0001)资助
Contributor Information
远洋 唐 (Yuan-yang TANG), Email: 13452670740@163.com.
高兴 罗 (Gao-xing LOU), Email: logxw@yahoo.com.
伟峰 贺 (Wei-feng HE), Email: heweifeng7412@aliyun.com.
References
- 1.徐溪, 莫乃新, 陈文美, 等 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与磺胺嘧啶银霜治疗深Ⅱ度烧伤的疗效观察. 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2016;16(4):486–488. [Google Scholar]
- 2.张彦标, 黄波, 李先慧, 等 某三甲医院烧伤病房烧伤感染的病原学特点. 西南军医. 2020;22(5):459–460. doi: 10.3969/j.issn.1672-7193.2020.05.016. [DOI] [Google Scholar]
- 3.SAPAN H B, PATURUSI I, JUSUF I, et al Pattern of cytokine (IL-6 and IL-10) level as inflammation and anti-inflammation mediator of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 in polytrauma. Int J Burn Trauma. 2016;6(2):37–43.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4.Ferrara J L Cytokine dysregulation as a mechanism of graft versushost disease. Cur Opinion Immunol. 1993;5(5):794–799. doi: 10.1016/0952-7915(93)90139-J.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5.刘军 对全身性感染免疫与炎症关系的思考.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2017;26(11):1230–1235. doi: 10.3760/cma.j.issn.1671-0282.2017.11.002. [DOI] [Google Scholar]
- 6.PANDOLFI F, ALTAMURA S, FROSALI S, et al Key role of DAMP in inflammation, cancer, and tissue repair. Clin Therap. 2016;38(5):1017–1028. doi: 10.1016/j.clinthera.2016.02.028.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7.ISHII K J, KOYAMA S, NAKAGAWA A, et al Host innate immune receptors and beyond: making sense of microbial infections. Cell Host Microbe. 2008;3(6):352–363. doi: 10.1016/j.chom.2008.05.003.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8.JESCHKE M G, BAAR M E V, CHOUDHRY M A, et al Burn injury. Nat Rev Dis Primer. 2020;6(1):12–36. doi: 10.1038/s41572-020-0152-6.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9.张林丽, 王艳, 刘莉 细胞因子与炎症免疫疾病的研究进展. 药学与临床研究. 2020;28(3):202–205. [Google Scholar]
- 10.陈虹瑾, 熊彬 IL-10对LPS诱导的急性肺损伤大鼠肺UGRP1及炎症因子的影响. 西南国防医药. 2020;30(3):194–197. doi: 10.3969/j.issn.1004-0188.2020.03.004. [DOI] [Google Scholar]
- 11.王嘉锋, 邓小明 脓毒症中性粒细胞功能障碍. 实用休克杂志(中英文) 2019;3(2):70–73. [Google Scholar]
- 12.MANTOVANI A, CASSATELLA M A, COSTANTINI C, et al Neutrophils in the activation and regulation of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ity. Nat Rev Immunol. 2011;11(8):519–531. doi: 10.1038/nri3024.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3.杨飞标 肿瘤坏死因子-α和白介素-6在急腹症合并多器官功能紊乱综合征中的变化研究. 中国医刊. 2013;48(4):68–70. doi: 10.3969/j.issn.1008-1070.2013.04.029. [DOI] [Google Scholar]
- 14.李世英, 李峥, 张晋霞, 等 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与脑梗死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2016;24(5):495–498. [Google Scholar]
- 15.ULLOA L, TRACEY K J The ‘cytokine profile’: a code for sepsis. Trend Mol Med. 2005;11(2):56–63. doi: 10.1016/j.molmed.2004.12.007.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6.李鸿明, 周金武, 毛高才, 等 重度烧伤创面免疫细胞变化与临床意义. 海南医学. 2016;27(16):2624–2626. doi: 10.3969/j.issn.1003-6350.2016.16.015. [DOI] [Google Scholar]
- 17.GABRILOVICH D I, NAGARAJ S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as regulators of the immune system. Nat Rev Immunol. 2009;9(3):162–174. doi: 10.1038/nri2506.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8.李诗, 杨志刚 MDSC的免疫调节机制及其在免疫治疗中的作用. 中国医学创新. 2017;14(13):140–144. doi: 10.3969/j.issn.1674-4985.2017.13.040. [DOI] [Google Scholar]
- 19.BAH I, KUMBHARE A, NGUYEN L, et al IL-10 induces an immune repressor pathway in sepsis by promoting S100A9 nuclear localization and MDSC development. Cell Immunol. 2018;332:32–38. doi: 10.1016/j.cellimm.2018.07.003.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20.BISWAS S K, CHITTEZHATH M, SHALOVA I N, et al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and plasticity in health and disease. Immunologic Res. 2012;53(1-3):11–24. doi: 10.1007/s12026-012-8291-9.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21.李春雨, 李晓菲, 涂灿, 等 基于内毒素模型的何首乌特异质肝损伤评价. 药学学报. 2015;50(1):28–33. [Google Scholar]
- 22.李春雨. 基于免疫应激的何首乌特异质肝损伤的初步研究. 成都: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5: 1-149.
- 23.陆二梅, 李益星, 白杨, 等 巨噬细胞极化的研究进展.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2016;16(32):6397–6400. [Google Scholar]
- 24.MURRAY P J, WYNN T A Protective and pathogenic functions of macrophage subsets. Nat Rev Immunol. 2011;11(11):723–737. doi: 10.1038/nri3073.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25.ARORA S, DEV K, AGARWAL B, et al Macrophages: their role, activation and polarization in pulmonary diseases. Immunobiology. 2017;223(4-5):383–396. doi: 10.1016/j.imbio.2017.11.001.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26.王东旭, 王虎, 周瀛, 等 巨噬细胞极化在炎性疾病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中国医药. 2017;12(9):1427–1430. doi: 10.3760/cma.j.issn.1673-4777.2017.09.040. [DOI] [Google Scholar]
- 27.SALES D S, ITO J T, ZANCHETTA I A, et al Regulatory T-cell distribution within lung compartments in COPD. COPD J Chron Obstruct Pulm Dis. 2017;14(5):533–542. doi: 10.1080/15412555.2017.1346069.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28.牛卓娅, 张亚玲, 姚智燕, 等 巨噬细胞极化与炎性疾病的研究进展. 河北医科大学学报. 2020;41(6):742–745. doi: 10.3969/j.issn.1007-3205.2020.06.028. [DOI] [Google Scholar]
- 29.MAUCOURANT C, QUEIROZ G A N, SAMRI A, et al Zika virus in the eye of the cytokine storm. Eur Cytok Network. 2019;30(3):74–81. doi: 10.1684/ecn.2019.0433.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30.CHEN H, WANG F, ZHANG P, et al Management of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related to CAR-T cell therapy. Front Med. 2019;13(5):610–617. doi: 10.1007/s11684-019-0714-8.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31.INDALAO I L, SAWABUCHI T, TAKAHASHI E, et al IL-1β is a key cytokine that induces trypsin upregulation in the influenza virus-cytokine-trypsin cycle. Arch Virol. 2017;162(1):201–211. doi: 10.1007/s00705-016-3093-3.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32.谷九龙, 李德龙, 王思媛, 等 病原性细菌阻断宿主补体系统激活的机制. 江西畜牧兽医杂志. 2018;(6):1–5. doi: 10.3969/j.issn.1004-2342.2018.06.001. [DOI] [Google Scholar]
- 33.季鸣, 王丽嫄, 金晶, 等 补体系统药物研究进展. 中国生化药物杂志. 2016;36(12):7–10. [Google Scholar]
- 34.李伟超, 张亭, 潘尉, 等 脓毒症患者血清微小RNA-21的水平变化及其意义. 山东医药. 2019;59(9):66–68. [Google Scholar]
- 35.MONK P N, SCOLA A M, MADALA P, et al Function, structure and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complement C5a receptors. Brit J Pharmacol. 2007;152(4):429–448. doi: 10.1038/sj.bjp.0707332.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36.韩交玲 强直性脊柱炎中HLA-B27表达及其与RF、外周血Th17细胞比率的关系. 中国疗养医学. 2019;28(5):476–478. [Google Scholar]
- 37.BERINGER A, NOACK M, MIOSSEC P IL-17 in chronic inflammation: from discovery to targeting. Trends Mol Med. 2016;22(3):230–241. doi: 10.1016/j.molmed.2016.01.001.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38.高艳彬, 卢志阳, 金辉, 等 小鼠烧伤后免疫细胞多功能紊乱的基因表达谱生物信息学分析. 广东医学. 2016;37(2):211–214. [Google Scholar]
- 39.常鑫, 袁颖, 王明义 Th1/Th2与PCT检测在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20;32(4):477–480. [Google Scholar]
- 40.王玉亮, 王峰, 耿洁 细胞因子与细胞因子风暴. 天津医药. 2020;48(6):494–499. [Google Scholar]
- 41.彭代智 我国烧伤免疫的研究. 中华烧伤杂志. 2008;24(5):390–392. doi: 10.3760/cma.j.issn.1009-2587.2008.05.025.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42.汪婷, 蒋政宇, 万小健, 等 冠状病毒肺炎细胞因子风暴及免疫调控治疗.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2020;41(8):818–823. [Google Scholar]
- 43.ADAMIK B, GOZDZIK W, JAKUBCZY D, et al Coagulation abnormalities identified by thromboelastometry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the relationship to endotoxemia and mortality. Blood Coagul Fibrinolysis. 2017;28(2):163–170. doi: 10.1097/MBC.0000000000000572.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44.张庆红, 姚咏明. 我国烧伤感染与免疫研究回顾和展望. 中华损伤与修复杂志(电子版), 2019, 14(5): 325-329[2020-10-02]. https://doi.org/10.3877/cma.j.issn.1673-9450.2019.0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