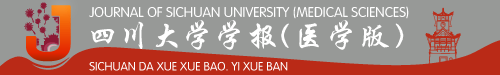Abstract
子痫前期-子痫是常见的产科危重症,是上百年来产科医生孜孜不倦研究和钻研的临床热点、难点。人们一直在探讨子痫前期-子痫的病因、病理、预防、干预及治疗手段,但是目前仍然没有参透它发生的原因,也难以找到有效的预防及治疗方法。虽然迷雾重重,研究的过程艰辛而坎坷,但我们也在逐步深入认识它,也许不久的将来能够透彻地理解这个疾病,更好地保障母胎平安。
Keywords: 子痫前期, 子痫, 诊断, 预防
Abstract
Preeclampsia-eclampsia is a common obstetric critical disease and obstetricians have studied it assiduously for hundreds of years. We have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etiology, pathology,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reeclampsia-eclampsia, but we still have not arrived at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its cause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thods. Although the research process has been fraught with difficulties and frustrations, we are nonetheless gradually gain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Perhaps, in the near future, we will be able to acquir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and find better ways to ensure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mothers and fetuses.
Keywords: Preeclampsia, Eclampsia, Diagnosis, Prevention
子痫前期-子痫(preeclampsia-eclampsia)严重威胁母儿健康和生命。在古代文献中就有关于子痫症状的描述,对子痫(eclampsia)的临床命名至少可以上溯到百年之前[1],但是虽然对子痫前期的研究历经了一个世纪之久,其发病机制仍然不清,临床表现多样,似乎除了终止妊娠以外仍缺乏有效治疗手段。不得不说,子痫前期-子痫是一个神秘的产科并发症,将产科医生置于层出不穷的难题面前,也敦促产科学者对它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探索。
1. 对子痫前期认识的变迁
对子痫前期的认识其实归根于人们对子痫的发现,换句话说,是人们先发现了子痫,再认识了子痫前期。子痫最早的描述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对它的首次记载出现在古希腊著名医学家Hippocrayes编写的著名的《希波克拉底全集》里,描述的是妊娠妇女抽搐和妊娠期间癫痫发作致死的病例。所有的早期医学家公认这是一种危险的疾病。1612年,Jacques Guillimeau认为孕妇抽搐是由于胎儿想奋力挣脱子宫或胎位不正,导致子宫扩张,从而引发抽搐[2]。 “Eclampsia”来自希腊语,据记载最早由Johannes Varandeus医生于1619年提出。1637年,产科先驱弗朗索瓦·莫里索(Francois Mauriceau)发表了对先兆子痫的最早临床描述,并被收入《人体疾病表征》数据库中,他指出了先兆子痫癫痫发作的高风险人群[3] 。 Mauriceau将子痫发作归因于恶露血流量异常或宫内胎儿死亡。他是第一个系统描述子痫的医生,由此表明该疾病引起了新的关注,他也是第一个提出初孕者比多次妊娠者发生子痫的风险更大。而对“Eclampsia”一词的具体解释则归功于法国医生和植物学家François Boissier de Sauvages de Lacroix[3] ,他首次提出了子痫与癫痫不同,癫痫为一种慢性疾病,存在于整个生命周期,且可反复发作,而子痫却不同[4] 。他认为,子痫发作是大自然试图摆脱“病态因素”的尝试。他首次根据产后症状的消退对癫痫和子痫做出了区分,这是对子痫认识的一个重要突破[5] 。
随着医学的进步和发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们对子痫前期的病因做出了更多猜测。如肾脏疾病/癫痫/妊娠毒血症或是一种被称为Bacillus eclampsiae的细菌入侵体内[6-7] ,亦或是来源于自身的毒性,认为可能是胎儿、母亲或胎盘的代谢产物[8]导致了子痫前期-子痫的发生。
19世纪,对该病的推测已经不胜枚举,医生们仍普遍认为先兆子痫-子痫是与妊娠相关的最可怕的疾病。1843年,John Lever进一步定义了先兆子痫,他发现患有先兆子痫的女性尿液中含有白蛋白,而Robert Johns则注意到这类患者出现了头痛、视力改变和水肿的特征性症状,这无疑对于子痫前期的认识是一个重大突破[5] 。John Lever对这个病症症状的描述已经接近现代。他认为该病其实是一种毒血症而并非由于子宫所受机械压力所致[6] 。直到20世纪,很多早期医学家都认为子痫好发于富裕女性,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贫穷女性子痫病例也被发现。在20世纪早期,尽管对子痫病因仍在多方推测,但人们已经认为子痫通常与高血压相关,并且能使血压升高[2]。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胎盘植入受损与先兆子痫有关,1989年ROBERTS等[9]假设先兆子痫患者中胎盘灌注受损导致广泛的母体内皮功能障碍。至此,广大产科工作者投入到了胎盘与子痫前期发生的基础研究的洪流中,逐渐形成了现在对子痫前期-子痫认识的基石。
2. 关于子痫前期的诊断
子痫前期的诊断和分类命名也几经变迁,这种变化伴随着产科医生对它认识的提升和改变,这种命名分类的变化也改变了产科医生对其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方向。
20世纪前,子痫前期有一个跨时代的曾用名叫做“妊娠中毒症”或“妊娠毒血症”。“毒血症”一词已逐渐弃用,但对“毒素”的研究仍在继续。随后的一些研究证实了高血压、蛋白尿和惊厥之间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发现了高血压和蛋白尿在抽搐发作前就已经存在,因此将这一疾病状态称之为“子痫前期”[5] 。1903年“子痫前期”被纳入教科书,临床开始广泛应用。1961年子痫前期-子痫一词仅用于产科疾病定义[10] 。在第15版Williams Obstetrics (1976)中,妊娠毒血症这一术语被妊娠高血压疾病所取代,同时先兆子痫的新分类包括在妊娠20周后开始出现高血压伴蛋白尿、水肿或两者兼有[11] 。国外逐渐根据临床症状将之命名为“水肿、蛋白尿、高血压综合征”,国内也在20世纪70年代后将之命名为“妊娠高血压综合征”[1]。这两种命名更多的是基于该病的临床表型。高血压和蛋白尿曾经一度是子痫前期诊断的必需指标,水肿也曾经作为子痫前期的三大主要临床表现之一。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ACOG)妊娠期高血压工作组于1972年引入了先兆子痫分类,并于2013年更新了该分类[12] 。2002年后,我国教科书与国际接轨,采纳了当时国际上较广泛用于临床的诊断标准和五分类法,将这个症候群命名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1],这也与当时的《威廉姆斯产科学》(22版)相同,分为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子痫、慢性高血压伴子痫前期及慢性高血压合并妊娠[1-2],取代了原来的“妊娠高血压综合征”这一命名。2008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科医学协会颁布的指南中将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分为4种: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子痫综合征(preeclampsia-eclampsia syndrome)、慢性高血压、慢性高血压伴发子痫前期[13]。在《威廉姆斯产科学》(23版)中仍可见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4分类法与5分类法均有,但在《威廉姆斯产科学》(24版)中则是4分类法,并且多次提到子痫前期综合征[1]。
在20世纪初,先兆子痫的定义发生了转变,蛋白尿从诊断的主导地位退居其次,以ACOG为代表的2013年版指南放弃了依赖蛋白尿来诊断子痫前期,而主要依据血压/母体的终末器官功能障碍以及胎儿不良结局,肾脏受累提升为其中之一[14] 。各国指南紧随其后也进行了更新,各个指南之间大同小异。如国际妊娠高血压研究学会(ISSHP)指南中也将子痫前期定义为妊娠高血压合并器官功能障碍,并在2021年明确提出不再区分“轻度”与“重度”子痫前期[13] 。我国的指南在2012年版中将子痫前期定义为妊娠高血压合并蛋白尿或器官功能障碍[15],直到2020版指南中对子痫前期的定义并未发生改变[16] ——2020年版指南定义子痫前期:妊娠20周后孕妇出现收缩压≥140 mmHg(1 mmHg=0.133 kPa)和(或)舒张压≥90 mmHg,伴有下列任意1项:尿蛋白定量≥0.3 g/24 h,或尿蛋白/肌酐比值≥0.3,或随机尿蛋白≥(+)(无条件进行蛋白定量时的检查方法);无蛋白尿但伴有以下任何1种器官或系统受累:心、肺、肝、肾等重要器官,或血液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的异常改变,胎盘-胎儿受到累及等[17]。因此,2020年版指南已经明确指出子痫前期可以无蛋白尿。回顾子痫前期命名及诊断的变迁史,每次改变都是因为对它认识得更深、更全面,随着研究的深入,或许不久后会迎来它新的命名和分类诊断。
3. 关于子痫前期的发生
对于子痫前期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研究,纵然国内外学者已辛勤摸索一个世纪,但仍不清楚。20世纪前,产科医生推测子痫的病因可能有孕期情绪波动,多血质、营养缺乏、肾功能不全、高血压、季节变换、忧郁症、富裕肥胖、情绪激动易怒等[2],当时的产科先驱们已经总结出了发生子痫前期-子痫的主要的高危因素。而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子痫前期的认识已经从简单的临床表现,渐渐深入到了其病理生理机制。提到子痫前期的发生机制,不得不提到风靡几十年的著名的子痫前期“二阶段模式”学说,该学说2009年由Redman提出,这也是目前公认的子痫前期发病机制[18] 。他认为是胎盘发育异常功能障碍和胎盘释放多种活性因子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引起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全身小动脉粥样硬化,从而使血管收缩舒张失衡致血压升高等,引发子痫前期一系列临床表型。随着对子痫前期发病机制研究的深入,Redman认为“二阶段模式”学说不能充分反应PE发病机制,又在2014年提出更加细化的“六阶段模式”。这个模式本质上是对“二阶段模式”学说作了更加细化的时间分段和内容补充。
妊娠期的疾病多由母胎直接和(或)间接冲突所致。遗传、环境及其交互作用引起母体免疫损伤和炎症紊乱,导致母胎冲突,出现临床症状。近几十年随着对子痫前期进一步的研究,目前的观点普遍认为子痫前期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胎盘缺血,炎症反应、应激反应、血管和内皮细胞功能障碍等亦参与了子痫前期的发生,以高血压、蛋白尿及其他脏器功能受损等为主要临床表现。子痫前期的发生是多因素的,不仅仅局限于胎盘病变,发病的通路也是多样化的,可以几种因素相互影响或触发。子痫前期不同系统和器官受累及,在不同个体间存在不平行性,换句话说,子痫前期的临床表现及病情程度存在明显个体差异,没有任何单一因素能够解释子痫前期病因和发病机制[19]。国外有学者曾提出“不典型子痫前期”的概念,实际上也是认为“子痫前期-子痫综合征”发病具有个体化及首发症状表现不一的特点[1, 20-21]。
总之,子痫前期具有高度异质性,母胎界面的组成极其复杂,各种类型细胞间的相互调控模式多种多样而且极其精细,要全面深入揭示子痫前期的病因机制非常困难,研究子痫前期仍然充满了挑战。
4. 关于子痫前期的治疗和预防
17世纪中叶,宗教文化的兴起,祈祷、信仰、奇迹等方法盛行。随着时间流逝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力降低,类似于远古时代治疗疾病的方法再次变得突出。1694年,Mauriceau建议如果在妊娠期间出现子痫发生的倾向,应常规进行2~3次静脉切开放血[2]。20世纪前多数产科医生认为子痫前期是由四种体液(血液、痰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不平衡、女性皮肤多孔或子宫在身体里游荡引起的,所以治疗的重点是恢复和维持体内平衡和健康,包括改变饮食、净化和放血。这些极端治疗手段,尤其是强调放血,无疑是孕妇死亡的主要原因[2]。随着对子痫前期发生机制、病因的不断认识,治疗也不断更新。18世纪后期疾病因果转向毒素理论,诊断为“妊娠期毒血症”,因此,治疗以消除过多的毒素为目标。随着生理病理学的发展,子痫前期的发病原因逐步转向为内皮损伤、胎盘螺旋动脉重铸障碍,管理上以住院、频繁测量血压和监测体质量、尿液检查、卧床休息、胎儿监护以及评估产妇自觉症状、减少刺激、加快阴道分娩、剖宫产、助产等护理/治疗方式出现。目前,认为子痫前期涉及氧化应激、胎儿胎盘单位和母体组织之间的免疫不耐受以及血管生成失衡的机制有关,但病因机制仍不能完全揭示,且对子痫前期缺乏有效的预防措施和筛查、预测工具,故子痫前期的病因治疗很难。
预测子痫前期是人们一直追求探索的事情。早在20世纪中上叶就有学者探讨孕期营养及抗凝方面的预防作用[1],不过似乎预防效果并不明显。直到1906年,首次出现静脉使用硫酸镁来治疗子痫前期,并随后得到推广。在20世纪后期开始给予硫酸镁和抗高血压药分别预防或控制惊厥和急性高血压。但至今治疗仍然更多地局限在解痉和对症方面,对子痫前期的治疗更多是被动医疗行为。小剂量阿司匹林(low dose aspirin, LDA)用于子痫前期的预防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子痫前期临床研究的主要成功案例之一[22]。最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GOODLIN等[23]报道一位有过2次妊娠均出现严重的胎儿生长受限(FGR)和子痫前期的患者,在第3次妊娠时,从孕22周开始每天口服阿司匹林(600 mg ,每天3次),此次妊娠在34周分娩出一个1410 g的男婴,健康存活。在这之后的数十年里,学者们进行了大量有关LDA预防子痫前期的随机对照研究,各研究中LDA用药适宜人群、开始用药的孕周、剂量以及用药时限等仍然存在不同观点[22],但很多国家仍将LDA预防子痫前期纳入指南。2018年国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研究会(ISSHP)推荐对存在子痫前期高危因素者,在孕20周前(最好是孕16周前)开始LDA治疗(75~162 mg/d)预防子痫前期[24] 。2019年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 )指南推荐PE高风险孕妇从妊娠11~14+6周使用LDA(每晚150 mg)直到孕36周、分娩时或被诊断为子痫前期为止[25] 。后来2019年NICE指南[26] 、2020年美国妇产科协会(ACOG )指南[14]均推荐孕12周开始口服LDA直至分娩,预防高危型患者发生子痫前期。我国2020年《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诊治指南》[16]提出对子痫前期高危患者从孕12~16周开始每天口服LDA(50~150 mg),依据个体因素决定用药时间,预防性应用可维持到孕26~28周[27]。各个国家指南都一致推荐LDA预防高危型患者子痫前期的发生,但是对于LDA停药孕周尚有争议,这是考虑到LDA对围分娩期的潜在风险,还需要高质量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探讨合适的停药时机。时至今日,LDA预防子痫前期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用药“模式化”,造成了LDA的过度使用和对子痫前期高危人群不加选择地使用,且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LDA的预防作用[22]。事实上,一些研究显示LDA预防性应用并未像预期那样明显降低子痫前期发病,使用LDA仅可使高危人群子痫前期发生率下降10%左右[22],目前的循证医学证据也认为LDA似乎仅对发生未足月子痫前期高风险的人群有一定预防价值,对于一些高危型患者(如大部分指南中认定的慢性高血压患者),并不能降低其发生子痫前期的风险。目前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妊娠期服用阿司匹林会增加产后出血和产后血肿的发生。它也可能与新生儿颅内出血有关。因此,我们应重视LDA应用的局限性和合理性[22]。
总之,对于子痫前期-子痫的研究可以说是从“临床-基础-临床实践”不停循环反复而又向前推进,但是子痫前期的发生仍然是未解之谜。就算是在三级医疗助产机构高质量的医疗保健下仍有子痫前期的发生,虽然规律产前检查仍有母儿不良事件发生、有产科相关的孕产妇死亡发生。或许我们可以综合研究生物信息学、遗传、环境等,以期发现更多和更好的生物标志物,来用于子痫前期的预防和治疗。子痫前期-子痫对于产科工作者来说,似乎一直是神秘而未解的,随着对其孜孜不倦地深入研究反而发现更多的问题,这何尝不是医学的魅力所在!
* * *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Funding Statement
国家卫计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No. 2016YFC1000406)资助
Contributor Information
国琳 何 (Guo-lin HE), Email: heguolin19@163.com.
兴会 刘 (Xing-hui LIU), Email: xinghuiliu@163.com.
References
- 1.杨孜 多因素、多通路、多机制致病解子痫前期综合征制胜真实世界临床实践.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017;33(1):45–51. [Google Scholar]
- 2.李方英, 华倩. 子痫的研究历程. 中国临床实用医学, 2010, 4(12): 196[2022-09-14]. https://doi.org/10.3760/cma.j.issn1673-8799.2010.12.137.
- 3.BOISSIER DE SAUVAGES DE LACROIX F. Pathologia methodica. Montpellier: Martel, 1739.
- 4.CHESLEY L C History and epidemiology of preeclampsia-eclampsia. Clin Obstet Gynecol. 1984;27(4):801–820. doi: 10.1097/00003081-198412000-00004.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5.BELL M J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preeclampsia-eclampsia. J Obstet Gynecol Neonatal Nurs. 2010;39(5):510–518. doi: 10.1111/j.1552-6909.2010.01172.x.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6.DELEE J B Theories of eclampsia. Am J Obstet. 1905;51:325–330. [Google Scholar]
- 7.LOUDON I Some historical aspects of toxaemia of pregnancy. A review. Br J Obstet Gynaecol. 1991;98(9):853–858. doi: 10.1111/j.1471-0528.1991.tb13505.x.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8.STANDER H J. The toxemias of pregnancy. Baltimore: The Williams & Wilkins Company, 1929.
- 9.ROBERTS J M, TAYLOR R N, MUSCI T J, et al Preeclampsia:An endothelial cell disorder. Am J Obstet Gynecol. 1989;161(5):1200–1204. doi: 10.1016/0002-9378(89)90665-0.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0.CHESLEY L C. Hypertensive disorders in pregnanc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78.
- 11.PRITCHARD J A, MACDONALD P C. Williams obstetrics. 15th.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76.
- 12.ACOG technical bulletin Hypertension in pregnancy. Number 219-January 1996 (replaces no. 91, February 1986).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ulletins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Int J Gynaecol Obstet. 1996;53(2):175–183. doi: 10.1016/S0020-7292(96)90112-5.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3.MAGEE L A, BROWN M A, HALL D R, et al. The 2021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Hypertension in Pregnancy classification, diagnosis & management recommend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practice. Pregnancy Hypertens, 2022 , 27: 148−169[2022-09-1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066406/. doi: 10.1016/j.preghy.2021.09.008.
- 14.TSAKIRIDIS I, GIOULEKA S, ARVANITAKI A, et al Gescational hypertension and preeclampsia : An overview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gaidelines. Obstet Gynecol Surv. 2021;76(10):613–633. doi: 10.1097/OGX.0000000000000942.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5.林其德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诊治指南(2012版)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12;47(6):476–480. [Google Scholar]
- 16.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学组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诊治指南(2020)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20;55(4):227–238. [Google Scholar]
- 17.庄旭, 林建华 尿蛋白在子痫前期诊断中的价值. 实用妇产科杂志. 2016;32(7):500–502. [Google Scholar]
- 18.JIM B, KARUMANCHI S A Preeclampsia: Pathogenesis, prevention, and long-term complications. Semin Nephrol. 2017;37(4):386–397. doi: 10.1016/j.semnephrol.2017.05.011.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9.杨孜 子痫前期多因素发病及多机制发病通路之综合征再认识. 中华医学杂志. 2015;95(1):7–9. doi: 10.3760/cma.j.issn.0376-2491.2015.01.003. [DOI] [Google Scholar]
- 20.杨孜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临床“对应性”问题.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012;28(4):245–247. [Google Scholar]
- 21.ROBILLARD P Y, DEKKER G, IACOBELLI S , et al. An essay of reflection: why does preeclampsia exist in humans, and why are there such hug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epidemiology? J Reprod Immunol, 2016, 114: 44−47[2022-09-1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6253618/. doi: 10.1016/j.jri.2015.07.001.
- 22.赫英东, 陈倩 阿司匹林预防子痫前期的局限性和临床应用选择.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021;37(5):519–522. [Google Scholar]
- 23.GOODLIN R C, HAESSLEIN H O, FLEMING J. Aspirin for the treatment of recurrent toxaemia. Lancet, 1978, 2(8079): 51[2022-09-1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78253/. doi: 10.1016/s0140-6736(78)91367-3.
- 24.BROWN M A, MAGEE L A, KENNY L C, et al Hypertensive disorders of pregnancy: ISSHP classification,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recommend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practice. Hypertension. 2018;72(1):24–43. doi: 10.1161/HYPERTENSIONAHA.117.10803.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25.POON L C, SHENNAN A, HYETT J A,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FIGO) initiative on pre-eclampsia: a pragmatic guide for first-trimester screening and prevention. Int J Gynaecol Obstet. 2019;145 Suppl 1(Suppl 1):1–33. doi: 10.1002/ijgo.12802.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26.WEBSTER K, FISHBURN S, MARESH M, et al.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hypertension in pregnancy: Summary of updated NICE guidance. BMJ, 2019, 366: l5119[2022-09-1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1501137/. doi: 10.1136/bmj.l5119.
- 27.黄桂琼, 刘兴会 子痫前期预防和预测的方法及评价. 实用妇产科杂志. 2020;36(12):885–888. [Google Sch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