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目的
评价骶神经调控(sacral neuromodulation,SNM)治疗脊柱裂患者神经源性膀胱和肠道功能障碍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 7 月—2021 年 5 月接受 SNM 治疗的 33 例脊柱裂致神经源性膀胱和肠道功能障碍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 19 例,女 14 例;年龄 18.5~36.5 岁,平均 26.0 岁。病程 12~456 个月,平均 195.8 个月。脊柱裂类型:隐性脊柱裂 8 例,脊膜膨出/脊髓脊膜膨出 25 例。临床症状:尿急-尿频 19 例,尿失禁 18 例,慢性尿潴留 27 例,肠道功能障碍 29 例。影像尿动力结果显示,4 例患者存在逼尿肌过度活动(detrusor overactivity,DO),29 例患者存在逼尿肌不活动(detrusor underactivity,DU)。5 条输尿管(4 例患者)存在膀胱输尿管反流(vesicoureteral reflux,VUR)。SNM 分为体验治疗期和永久植入,体验治疗结束后评估为成功或愿意永久植入的患者,将永久脉冲发生器植入体内。
结果
体验治疗期持续时间 14~28 d,平均 19.2 d;期间未出现并发症,总体成功率为 69.69%(23/33)。体验治疗结束时,有下尿路症状患者 24 h 排尿次数、每次排尿量、尿急程度评分及漏尿量均较体验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体验治疗前后残余尿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383,P=0.179)。慢性尿潴留患者体验治疗后改善超过 50% 的比例为 25.93%,明显低于尿急-尿频(63.16%)和尿失禁(61.11%)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260,P=0.064)。尿动力学参数最大膀胱容量、膀胱顺应性较治疗前增加,充盈期最大逼尿肌压力较治疗前减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4 例治疗前存在 DO 的患者中 2 例 DO 消失;27 例治疗前存在 DU 者均未在排尿期恢复逼尿肌正常收缩。治疗前出现 VUR 的 5 条输尿管中,体验治疗结束时有 2 条 VUR 消失,其余 3 条的 VUR 等级或出现 VUR 时的膀胱容量均有所改善。体验治疗结束时,患者神经源性肠功能障碍(NBD)评分及肠道功能障碍等级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共 19 例患者接受了永久植入,其中 11 例患者需要结合间歇导尿的方式排空膀胱。
结论
SNM 治疗脊柱裂患者神经源性膀胱和肠道功能障碍有效,同时可显著改善患者储尿期的尿动力学参数,避免上尿路损坏。
Keywords: 骶神经调控, 脊柱裂, 神经源性膀胱, 肠道功能障碍, 尿动力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sacral neuromodulation (SNM) in the treatment of neurogenic bladder and bowel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pina bifida.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3 patients with neurogenic bladder and bowel dysfunction caused by spina bifida treated with SNM between July 2012 and May 2021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re were 19 males and 14 femal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26.0 years (range, 18.5-36.5 years). The disease duration ranged from 12 to 456 months, with an average of 195.8 months. The types of spina bifida included 8 cases of occult spina bifida and 25 cases of meningocele/myelomeningocele. Clinical symptoms included 19 cases of urgency-frequent urination, 18 cases of urinary incontinence, 27 cases of chronic urinary retention, and 29 cases of bowel dysfunction. Image urodynamics showed that 4 patients had detrusor overactivity (DO) and 29 patients had detrusor underactivity (DU). Vesicoureteral reflux (VUR) was found in 5 ureters (4 patients). SNM procedure was divided into experiential treatment and permanent implantation. Patients who were evaluated as successful or willing to be permanently implanted after experiential treatment would implant the permanent pulse generator.
Results
The duration of experiential treatment was 14-28 days, with an average of 19.2 days; there was no complic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e overall success rate was 69.69% (23/33). At the end of experiential treatment, the urination frequency in 24 hours, urine volume per time, urinary urgency score, and urine leakage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experiential treatment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ostvoid residual volume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experiential treatment (t=1.383, P=0.179). The success rate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urinary retention after experiential treatment (25.93%)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urgency-frequent urination (63.16%) and urinary incontinence (61.11%) (χ2=7.260, P=0.064).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experiential treatment, the maximum cystometric capacity and compliance increased and the maximum detrusor pressure during filling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Among the 4 patients with DO before experiential treatment, DO disappeared in 2 cases; 27 patients with DU before experiential treatment did not recover the normal contraction of detrusor during micturition. Among the 5 ureters with VUR before experiential treatment, 2 VUR disappeared at the end of experiential treatment, and the VUR grade or the bladder volume before VUR of the other 3 ureters were improved. At the end of experiential treatment, the neurogenic bowel dysfunction (NBD) score and the grade of bowel dysfunc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A total of 19 patients received permanent implantation, of which 11 patients needed to empty the bladder in combination with intermittent catheterization.
Conclusion
SNM is effective for neurogenic bladder and bowel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pina bifida.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urodynamic parameters during urine storage and avoid upper urinary tract damage.
Keywords: Sacral neuromodulation, spina bifida, neurogenic bladder, bowel dysfunction, urodynamics
脊柱裂是由于胚胎早期发育过程中尾神经管不能正常融合引起的,全世界新生儿脊柱裂发病率为 0.03%~0.05%[1]。根据融合异常的严重程度和病变位置,脊柱裂可分为隐性脊柱裂、脊膜膨出和脊髓脊膜膨出 3 种类型[2]。由于骶骨的神经管未完全闭合,部分或全部脊髓内容物通过背侧缺损突出,可导致各种神经功能缺失。对骶神经支配膀胱的躯体传入成分、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的影响可直接导致膀胱和肠道功能障碍,并最终由于膀胱动力不足、膀胱腔内高压而损害上尿路功能。因此,泌尿系统问题是脊柱裂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在长期随访的开放性脊柱裂患者中,约 1/3 患者的死亡与泌尿系统疾病有关[3]。
为了保护肾功能,脊柱裂患者从出生起就必须保持膀胱低压。膀胱管理依赖于间歇导尿(intermittent catheterization,IC)[4]和口服抗胆碱能药物或逼尿肌注射 A 型肉毒毒素(botulinum toxin type A,BTX-A)[5]。但是,许多患者对这些治疗无效或无法耐受其副作用。目前,骶神经调控(sacral neuromodulation,SNM)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神经源性膀胱患者中,尤其在不完全脊髓损伤[6]以及多发性硬化患者[7]中取得了一定疗效。近年来,一些脊柱裂患者也接受了 SNM 治疗。然而,脊柱裂患者的神经病变是先天性的,与外伤性脊髓损伤或多发性硬化并不相同。本研究通过回顾分析 2012 年 7 月—2021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 SNM 电极植入并进行体验治疗的 33 例脊柱裂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临床资料,旨在评价 SNM 治疗脊柱裂患者神经源性膀胱和肠道功能障碍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19 例,女 14 例;年龄 18.5~36.5 岁,平均 26.0 岁。病程 12~456 个月,平均 195.8 个月。患者均有明确脊柱裂病史;主诉为下尿路症状伴或不伴肠道功能障碍,抗胆碱能药物和逼尿肌注射 BTX-A 无效或不能耐受;无上尿路功能损害,无严重心理障碍或使用轮椅患者。脊柱裂类型:隐性脊柱裂 8 例,脊膜膨出/脊髓脊膜膨出 25 例。20 例有脊柱裂手术史。根据排尿情况并参照国际尿控学会(ICS)标准化定义[8],将患者临床症状分为尿急-尿频、尿失禁和慢性尿潴留,本组尿急-尿频 19 例,尿失禁 18 例,慢性尿潴留 27 例。肠道功能障碍 29 例。
1.2. 治疗方法
1.2.1. 治疗前准备
患者治疗前均接受详细的临床评估,包括完整病史、体格检查、泌尿系超声、影像尿动力学和骶尾骨 CT 三维重建检查。在进行 SNM 体验治疗前,记录有下尿路症状患者 3 d 的排尿情况,包括尿急-尿频者 24 h 排尿次数、每次排尿量、尿急程度评分[8],尿失禁者漏尿量(通过尿垫重量增加计算),以及慢性尿潴留者残余尿量(post-void residual volume,PVR;采用导尿法测量)。
影像尿动力学检查参照 ICS 尿动力学实践指南[8]。记录尿动力学参数,包括最大膀胱容量(maximum cystometric capacity,MCC)、充盈期最大逼尿肌压力、最大尿流率(Qmax),并计算膀胱顺应性[9];判断逼尿肌过度活动(detrusor overactivity,DO)或逼尿肌不活动(detrusor underactivity,DU),本组 4 例患者治疗前存在 DO,29 例患者在排尿期存在 DU,依靠腹压排尿;膀胱输尿管反流(vesicoureteral reflux,VUR)参照国际反流分类标准[10],本组治疗 66 条输尿管中有 5 条(4 例)出现了 VUR。
采用神经源性肠功能障碍(NBD)评分评价患者肠道功能[11]。本组治疗前 29 例存在肠道功能障碍,NBD 评分为 12.0(9.0,14.5)分;肠道功能障碍重度 8 例、中度 13 例、轻度 4 例、非常轻度 4 例。
33 例患者中有 17 例在体验治疗前及治疗期间一直服用抗胆碱能药物。
1.2.2. 治疗方法
SNM 分为体验治疗期和永久植入[12]。在体验治疗前先进行电极植入。患者于局麻下取俯卧位,X 线透视下,将电极(Intersim 3093 型;美敦力公司,美国)放置在合适的骶神经根(通常是 S3)。如果术前评估发现患者有严重骶尾骨畸形,穿刺时使用 CT[13](本组 7 例)或 3D 打印导航模板[14](本组 9 例)引导穿刺针进入目标骶孔。电极植入后连接体外刺激盒,并设置参数(推荐参数:频率 14 Hz,脉宽 210 ms,根据患者反应设置电压幅度)。本组所有患者均接受了单侧电极植入并测试,体验治疗期一般为 2~4 周。
体验治疗结束后,对患者进行重新评估,包括泌尿系超声、影像尿动力学检查、排尿情况(3 d)、PVR(3 次)和 NBD 评分。体验治疗成功定义[15]:与术前相比,24 h 排尿次数、每次排尿量、尿急程度、漏尿量或者 PVR 中至少 1 项改善超过 50%。永久脉冲发生器的植入标准是体验治疗成功或患者愿意永久植入。
永久植入阶段,将脉冲发生器(Intersim 3058 型;美敦力公司,美国)植入患者体内,与体验治疗阶段植入的电极相连。体外程控仪测试阻抗,如都正常,关闭切口。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GraphPad Prism 8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满足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不满足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符号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临床症状
体验治疗期持续时间 14~28 d,平均 19.2 d。体验治疗阶段未出现感染、移位等并发症。体验治疗结束时,有下尿路症状患者 24 h 排尿次数、每次排尿量、尿急程度评分及漏尿量均较体验治疗前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体验治疗前后 PVR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383,P=0.179)。见表 1。其中,尿急-尿频、尿失禁、慢性尿潴留患者体验治疗后改善超过 50% 的比例分别为 63.16%(12/19)、61.11%(11/18)、25.93%(7/27),慢性尿潴留患者明显低于尿急-尿频和尿失禁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260,P=0.064)。本组体验治疗总体成功率为 69.69%(23/33)。其中 8 例患者因不满意未获得全部症状改善,未进行永久植入。余 15 例患者进行了永久植入,其中 8 例有多种症状并存者,体验治疗后所有症状均改善;7 例储尿期症状(尿急-尿频和/或尿失禁)获得改善,但 PVR 无明显下降,也接受永久植入并结合 IC 排空膀胱。
表 1.
Comparison of micturition in patients with lower urinary tract symptoms before and after experiential treatment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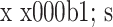 )
)
体验治疗前后有下尿路症状患者排尿情况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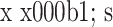 )
)
| 排尿情况
Micturition |
例数
n |
体验治疗前
Before experiential treatment |
体验治疗后
After experiential treatment |
统计值
Statistic |
| 24 h 排尿次数
Urination frequency in 24 hours |
19 | 14.6±3.5 | 9.7±2.2 |
t=7.128
P=0.000 |
| 每次排尿量(mL)
Urine volume per time(mL) |
19 | 116.1±33.3 | 193.0±49.4 |
t=7.544
P=0.000 |
| 尿急程度评分
Urinary urgency score |
19 | 3.4±0.8 | 1.9±0.9 |
t=6.851
P=0.000 |
| 漏尿量(mL)
Urine leakage(mL) |
18 | 185.2±139.2 | 94.72±104.8 |
t=5.605
P=0.000 |
| PVR(mL) | 27 | 168.1±128.2 | 150.4±129.9 |
t=1.383
P=0.179 |
2.2. 尿动力学参数
体验治疗结束时,尿动力学参数 MCC、顺应性较治疗前增加,充盈期最大逼尿肌压力较治疗前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4 例治疗前存在 DO 的患者中 2 例 DO 消失,另 2 例 DO 仍然存在。27 例治疗前存在 DU 者,体验治疗结束时,尽管 Qmax 从(6.481±3.652)m/s 增加至(10.190±3.101)m/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250,P=0.000),但均未在排尿期恢复逼尿肌正常收缩。治疗前出现 VUR 的 5 条输尿管中,体验治疗结束时有 2 条 VUR 消失,其余 3 条的 VUR 等级或出现 VUR 时的膀胱容量均有所改善。见表 3。该 4 例术前出现 VUR 的患者因 VUR 消失或改善而接受了永久植入,同时结合 IC 排空膀胱。
表 2.
Comparison of urodynamic parameters before and after experiential treatment (n=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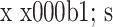 )
)
体验治疗前后尿动力学参数比较(n=33,
 )
)
| 参数
Parameter |
体验治疗前
Before experiential treatment |
体验治疗后
After experiential treatment |
统计值
Statistic |
| 注:1 cm H2O=0.098 kPa
Note: 1 cm H2O=0.098 kPa | |||
| MCC(mL) | 217.5±124.3 | 289.2±110.9 |
t=4.461
P=0.000 |
| 膀胱顺应性(mL/cm H2O)
Bladder compliance(mL/cm H2O) |
9.41±6.84 | 20.14±15.15 |
t=4.220
P=0.000 |
| 充盈期最大逼尿肌压力(cm H2O)
Maximum detrusor pressure during filling(cm H2O) |
42.27±29.33 | 26.81±20.32 |
t=6.426
P=0.000 |
表 3.
Changes of VUR before and after experiential treatment in 4 patients
4 例患者体验治疗前后 VUR 变化情况
| 序号
No. |
输尿管侧别
Side of ureter |
体验治疗前
Before experiential treatment |
体验治疗后
After experiential treatment |
|||
| VUR 等级
VUR grade |
出现 VUR 时的容量(mL)
The volume before VUR(mL) |
VUR 等级
VUR grade |
出现 VUR 时的容量(mL)
The volume before VUR(mL) |
|||
| 1 | 左 | Ⅱ | 42 | Ⅰ | 120 | |
| 2 | 右 | Ⅱ | 195 | 消失 | − | |
| 3 | 左 | Ⅲ | 45 | Ⅰ | 149 | |
| 4 | 左 | Ⅳ | 70 | Ⅰ | 75 | |
| 右 | Ⅰ | 227 | 消失 | − | ||
2.3. 肠道功能
体验治疗结束时,29 例有肠道功能障碍患者 NBD 评分为 6.0(3.0,8.0)分,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169.500,P=0.000)。肠道功能障碍等级为重度 3 例、中度 3 例、轻度 7 例、非常轻度 16 例,较术前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16.540,P=0.001)。其中 4 例肠道功能改善而下尿路功能无改善者未选择永久植入。
2.4. 永久植入术后疗效
最终共 19 例患者(57.58%)接受了永久植入,有 8 例患者在接受 SNM 治疗同时还服用了抗胆碱能药物,以提高后续治疗效果。永久植入术后随访时间 2~108 个月,平均 38.2 个月。8 例永久植入术后仍自主排尿的患者中,3 例出现新的 2 级 VUR 而改行 IC 联合口服抗胆碱能药物;2 例因上尿路严重损坏行肠道膀胱扩大术,术后结合 IC 排空膀胱;3 例仍自主排尿,定期复查。其余 11 例永久植入后采取 IC 患者维持原有疗效。
3. 讨论
SNM 是一种微创治疗顽固性下尿路功能障碍的方法,通过刺激骶神经的躯体传入成分抑制膀胱副交感节前神经元、盆神经向膀胱的传出,激活脊髓中协调膀胱和括约肌功能的中间神经元,促进排空,同时也能抑制由 C 纤维传导通路介导的膀胱过度反射[6]。因此,其适应证为尿急-尿频综合征、急迫性尿失禁、非梗阻性尿潴留以及大便失禁。近年来,国内外很多学者利用 SNM 改善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下尿路症状,取得了一定疗效。然而,神经源性膀胱是一类因神经系统疾病导致的下尿路功能障碍,病因多种多样,每种病因导致的神经源性膀胱其病理生理可能有所不同。因此,SNM 对不同病因导致的神经源性膀胱的疗效也应有所不同。
目前,针对 SNM 在不完全脊髓损伤和多发性硬化患者中的应用研究比较多,在脊柱裂患者中的应用研究很少。我们既往研究评估了 SNM 治疗脊髓疾病或损伤患者的临床效果[16],其中包括 12 例脊柱裂患者,但只关注了临床症状的改善。本研究对 33 例脊柱裂患者的临床症状、NBD 评分、尿动力学参数改变等进行了详细评价。与其他脊髓损伤患者的下尿路症状相似,脊柱裂患者通常也是多种下尿路症状(尿急-尿频、尿失禁、慢性尿潴留)并存,伴或不伴肠道症状(大便失禁、便秘)。SNM 有时不能改善患者所有症状,但如果能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依然可以将脉冲发生器永久植入体内,同时结合其他治疗方式(如 IC)。本研究中,19 例患者(57.58%)接受了永久脉冲发生器植入,其中 11 例患者 PVR 未明显减少,但由于储尿期症状或 VUR 情况明显改善,因此也选择了永久植入,术后结合 IC 排空膀胱,生活质量仍有所提高。
在既往研究中,我们还评估了患者的便秘情况[16]。然而,脊柱裂患者往往同时有便秘和大便失禁[17],只评估便秘情况并不全面。因此本研究使用 NBD 评分评估患者的便秘、大便失禁和生活质量。NBD 评分量表涵盖了对神经源性肠道功能障碍便秘、大便失禁情况的评估调查,并已在不完全脊髓损伤以及脊柱裂患者中验证了其效度。本研究中,NBD 评分从体验治疗前的 12.0(9.0,14.5)分显著下降至治疗结束时的 6.0(3.0,8.0)分(P<0.05);同时,肠道功能障碍等级减轻(Z=16.540,P=0.001)。虽然有 4 例肠道功能改善明显但下尿路功能无改善者未选择永久植入,但我们相信在将来肠道功能的改善可能作为永久植入指标之一,用于评估 SNM 治疗神经源性膀胱疗效。
为了保护肾功能,脊柱裂患者从出生起就必须保持膀胱低压[18]。因此,与临床症状改善相比,储尿期功能改善更为重要。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尿动力学评价了 SNM 对储尿期的影响。体验治疗结束时,患者的 MCC、膀胱顺应性和储尿期最大逼尿肌压力均明显改善,直接导致部分患者 VUR 消失或缓解。体验治疗前 66 条输尿管中有 5 条(4 例患者)出现了 VUR,治疗结束时 2 条 VUR 消失,另 3 条的 VUR 分级或出现 VUR 时的容积均有所改善,符合开展 IC 的条件。因此,该 4 例患者均接受了永久植入,并联合 IC 排空膀胱。
本研究中,只有 4 例患者有 DO,但 18 例患者有尿失禁症状。在脊柱裂患者中,尿失禁除了由 DO 导致,还可能由尿道闭合功能障碍以及膀胱顺应性低等因素引起。然而,无论是何种原因或多种原因导致的尿失禁,SNM 都可以通过改善膀胱顺应性、降低膀胱压力、增大膀胱容量来减轻尿失禁,同时也能减少对上尿路的损害。
在排尿期,虽然 Qmax 从(6.481±3.652)m/s 增加至(10.190±3.101)m/s(P<0.05),但尿动力学检查显示所有患者均未恢复逼尿肌正常收缩。尽管有 8 例患者在永久性植入术后可自主排尿,但仍依靠腹压排尿,因此存在上尿路损坏的高风险。在长期随访中,有 3 例患者因新发 VUR 改用 IC 联合抗胆碱药治疗,2 例因上尿路严重损坏行肠道膀胱扩大术。因此,我们认为 IC 仍是 DU 患者永久性植入术后最安全的方法[19]。此外,永久性植入术后的尿动力学评估以及定期随访是非常必要的。
脊柱裂患者大多有骶尾骨畸形,因此必须事先评估穿刺能否正常进行,否则需要其他方法辅助穿刺。本研究中,因骶尾骨畸形,7 例患者(21.21%)于 CT 引导下穿刺,9 例患者(27.27%)于 3D 打印导航模板引导下穿刺。
综上述,SNM 对脊柱裂患者的神经源性膀胱和肠道功能障碍有效。同时,SNM 可以显著改善此类患者在储尿期的尿动力学参数,避免上尿路损坏。
作者贡献:陈国庆负责实验设计及实施、数据收集整理、统计分析以及文章撰写;王祎明、英小倩、庞冬清负责数据收集整理;廖利民负责实验设计以及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在课题研究和文章撰写过程中不存在利益冲突。课题经费支持没有影响文章观点和对研究数据客观结果的统计分析及其报道。
机构伦理问题:研究方案经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2020-131-1)。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Funding Statement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课题(2019zx-08)
Project of China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Center (2019zx-08)
Contributor Information
国庆 陈 (Guoqing CHEN), Email: cgq_2000@126.com.
利民 廖 (Limin LIAO), Email: lmliao@263.net.
References
- 1.Mitchell LE, Adzick NS, Melchionne J, et al Spina bifida. Lancet. 2004;364(9448):1885–1895. doi: 10.1016/S0140-6736(04)17445-X.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2.Copp AJ, Adzick NS, Chitty LS, et al. Spina bifida. Nat Rev Dis Primers, 2015, 1: 15007. doi: 10.1038/nrdp.2015.7.
- 3.Moussa M, Papatsoris AG, Chakra MA, et al Perspectives on urological care in spina bifida patients. Intractable Rare Dis Res. 2021;10(1):1–10. doi: 10.5582/irdr.2020.03077.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4.Sager C, Barroso U, Bastos JM, et al. Management of neurogenic bladder dysfunction in children update and recommendations on medical treatment. Int Braz J Urol, 2021, 47. doi: 10.1590/S1677-5538.IBJU.2020.0989.
- 5.Hascoet J, Manunta A, Brochard C, et al Outcomes of intra-detrusor injections of botulinum toxin in patients with spina bifida: A systematic review. Neurourol Urodyn. 2017;36(3):557–564. doi: 10.1002/nau.23025.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6.Averbeck MA, Moreno-Palacios J, Aparicio A Is there a role for sacral neuromod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neurogenic lower urinary tract dysfunction? Int Braz J Urol. 2020;46(6):891–901. doi: 10.1590/s1677-5538.ibju.2020.99.10.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7.Rahnama’i MS Neuromodulation for functional bladder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sclerosis. Mult Scler. 2020;26(11):1274–1280. doi: 10.1177/1352458519894714. [DOI] [PMC free article] [PubMed] [Google Scholar]
- 8.Abrams P, Cardozo L, Fall M, et al The standardisation of terminology of lower urinary tract function: report from the Standardisation Sub-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inence Society. Neurourol Urodyn. 2002;21(2):167–178. doi: 10.1002/nau.1930110603.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9.Schäfer W, Abrams P, Liao L, et al Good urodynamic practices: uroflowmetry, filling cystometry, and pressure-flow studies. Neurourol Urodyn. 2002;21(3):261–274. doi: 10.1002/nau.10066.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0.Lebowitz RL, Olbing H, Parkkulainen KV, et al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radiographic grading of vesicoureteric reflux. International Reflux Study in Children. Pediatr Radiol. 1985;15(2):105–109. doi: 10.1007/BF02388714.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1.Chen G, Liao L, Wang Y, et al Effect of sacral neuromodulation on bowel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neurogenic bladder. Colorectal Dis. 2020;22(12):2155–2160. doi: 10.1111/codi.15273.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2.Dodge NA, Linder BJ Techniques for optimizing lead placement during sacral neuromodulation. Int Urogynecol J. 2020;31(5):1049–1051. doi: 10.1007/s00192-019-04208-0.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3.Amoroso L, Pelliccioni G, Ghiselli R, et al Sacral-neuromodulation CT-guided. Radiol Med. 2005;109(4):421–429.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4.Zhang J, Zhang P, Wu L, et al Application of an individualized and reassemblable 3D printing navigation template for accurate puncture during sacral neuromodulation. Neurourol Urodyn. 2018;37(8):2776–2781. doi: 10.1002/nau.23769.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5.Chen G, Liao L, Wang Y, et al Urodynamic findings during the filling phase in neurogenic bladder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vesicoureteral reflux who have undergone sacral neuromodulation. Neurourol Urodyn. 2020;39(5):1410–1416. doi: 10.1002/nau.24354.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6.Chen G, Liao L Sacral neuromodulation for neurogenic bladder and bowel dysfunction with multiple symptoms secondary to spinal cord disease. Spinal Cord. 2015;53(3):204–208. doi: 10.1038/sc.2014.157.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7.Ambartsumyan L, Rodriguez L Bowel management in children with spina bifida. J Pediatr Rehabil Med. 2018;11(4):293–301. doi: 10.3233/PRM-170533.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8.Le HK, Cardona-Grau D, Chiang G Evaluation and long-term management of neurogenic bladder in spinal dysraphism. Neoreviews. 2019;20(12):e711–e724. doi: 10.1542/neo.20-12-e711.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 19.Zemirline A, Vincent JP, Sid-Ahmed S, et al Lumbo-sacral malformations and spina bifida occulta in medieval skeletons from Brittany. Eur J Orthop Surg Traumatol. 2013;23(2):149–153. doi: 10.1007/s00590-012-0967-2. [DOI] [PubMed] [Google Scholar]


